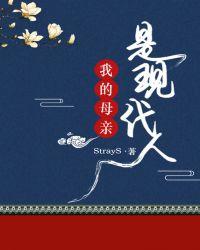凤阅居>古典制约by蒸汽桃讲了什么 > 第68頁(第2页)
第68頁(第2页)
他臉有點熱,「那沙發是學校配的,可能年頭也早了。」
「這沒什麼,正好今天下午有熬夜戲碼,」牧長覺沖他笑笑,「正合適。」
--
在燕知詢問可不可以帶著牧長覺一起談話的郵件里,薛鏡安簡單秒回了一個「那太好了」。
在她進來的時候,燕知又跟她說明了一下,「這是我同事牧長覺,因為有一些角色塑造的需要,他想要旁聽我們的對話,但對於內容他是絕對保密的。」
「完全沒問題,」薛鏡安大大方方地回答:「我磕你們的cp很久了。」
一句話里有倆生詞。
燕知不知道「磕」和「cp」是什麼意思。
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牧長覺。
牧長覺一直保持著傾聽的姿態,在女孩說了那句話之後也沒有任何神態的變化。
燕知估計那句話沒什麼特別的意思,只是稍微清了清嗓子,「好,那我們就說正事兒。」
哪怕放在風華正茂的年輕女孩當中,薛鏡安也是出類拔萃的漂亮,尤其是目光中有種頭腦清晰的敏銳犀利。
燕知一開口,她立刻就撿出來她覺得最重要的事,「如果您對我父親有任何成見,或者擔心受到我父親的任何影響,都不用勉強收留我。我退學也沒關係。不搞科研,我也有的是路走。」
她語氣挺強硬的,眼睛卻沒看著燕知。
「那些事對我不重要。」燕知似乎完全沒介意她的態度,「你父親怎麼樣,你退不退學,都跟我沒關係,不屬於正事兒。」
房間裡的另外兩雙眼睛一起望著他。
燕知在工作的時候習慣了完全屏蔽情感,對於他們的注視非常坦然,「我想聊的正事兒,指的是你對從免疫跨到神經的困難接受程度,以及對可能後果的容錯率。」
他想了想又糾正,「你接受退學說明你有能力承受消極後果,這很好。」
他幾句話把薛鏡安的認知刷了,「燕老師,你知道我爸的情況和我的處境嗎?如果我來你實驗室,基金委那幫孫子很難說不針對你。」
「這是我要處理的問題,不需要和你溝通。」燕知在這種事上不拐彎抹角,「你看過我發表的文章嗎?」
「看過。」薛鏡安答得乾脆,「從您博士期間發表的七篇一作文章到博士後期間的全部文章,我都通讀過了。」
「好。」燕知覺得這樣聊天就輕鬆多了,「那你對哪一部分最感興?」
他現在的工作主體是博士後時期的延續。
薛鏡安的興是他對接下來工作安排的重要參考項。
「成癮。」薛鏡安早就準備好了答案,「您在博士期間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關於解除古典制約的。後續的系列文章,包括非藥物性物質的渴求抑制和對精神渴望的主觀抑制,都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