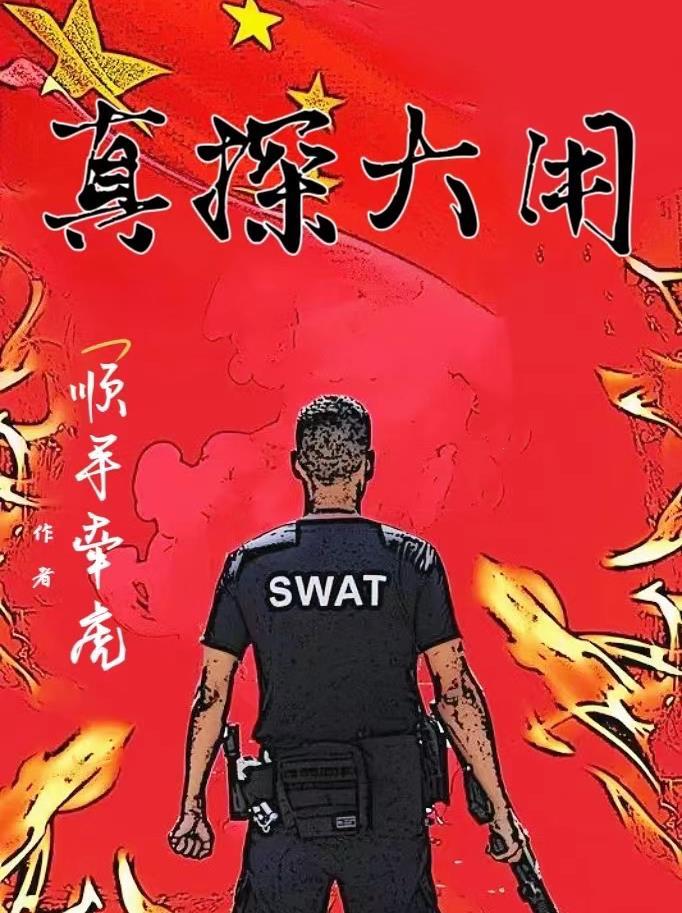凤阅居>古典制约by蒸汽桃讲了什么 > 第77頁(第2页)
第77頁(第2页)
夢好像比幻象還要好,只可惜不是想做就做。
淋浴間的門打開的時候,燕知嚇得整個人往被子裡一縮。
牧長覺披著浴袍出來,快步走到床邊,「怎麼了?」
燕知的心臟一直突突,但他的理智還在。
他開始快回溯昨晚的事,以免眼前這個人是真的存在。
「燕老師做噩夢了?」牧長覺撫摸著他的背,「我開門嚇著你了?」
燕知捕捉到了那一聲「燕老師」,想起來昨天臨睡前牧長覺也一直叫他「燕老師」的。
他擅自定下一條分水線。
「沒什麼,睡得有點糊塗而已。」燕知掩飾著,抬手把自己的頭髮隨意扎了起來,「牧先生,昨晚休息得還好嗎?」
牧長覺用毛巾揉著還滴水的頭髮,「挺好的,燕老師睡相很好。」
他沒提燕知一整晚都像鎖喉一樣箍著他的事。
牧長覺走到書桌前坐下,「燕老師要想醒醒神,有空幫我吹一下頭髮嗎?」
「我也沖個澡,你自己吹吧。」燕知背過身穿拖鞋,不想看牧長覺。
「我不大會用吹風機,上次把脖子上吹出一個水泡,到現在還能看見疤。」牧長覺稍微扒開耳後的頭髮,露出後腦上一處猙獰的短疤。
只是平常有頭髮擋著,也不大,不特地去看去摸很難發現。
但那傷疤的位置一看就極為兇險,但凡要在一個寸勁上,說要人命就要人命。
燕知立刻湊近了看,「這怎麼弄的?這不是燙的。」
他皺著眉,「你碰到哪兒了?」
「怎麼不是燙的?這就是我沒拿好吹風機,被出風口燙的。」牧長覺仰著頭看他,「當時可疼了,燕老師給吹吹。」
燕知還在仔細看那處疤,想著得是什麼東西才能傷成這樣,心不在焉地用嘴吹了兩下。
牧長覺笑著清了清嗓子,「我是說,燕老師幫我用吹風機吹一下頭髮。」
燕知反應了一下,紅著臉要往後退,「你用毛巾擦乾淨。」
「燕老師,」牧長覺頭都沒回就把他的手抓住了,「昨天才下了雨,外面好涼。頭髮不干透我就要生病了,劇組又得停工好幾天。」
燕知被他抓得心慌意亂,最後把吹風機接過來了。
他用手背試了一下溫度,從前往後地給牧長覺吹頭髮。
小時候都是牧長覺給他吹頭髮,燕知有時候喜歡把手指往他剛吹乾的頭髮里插,卻並不知道他頭髮潮濕時的觸感。
燕知認認真真地吹著,在牧長覺的鬢角發現了一根白髮。
他看著那根白頭髮,就像是看著點牧長覺的細紋一樣,心裡有點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