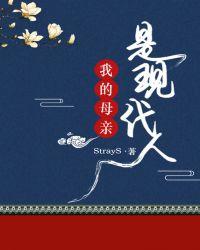凤阅居>古典制约by蒸汽桃讲了什么 > 第84頁(第1页)
第84頁(第1页)
燕知聽人家講了幾回,親自去診所的錢都省了。
在國外那幾年過下來,他也只有兩次急救是因為發燒,是小概率事件。
幻象也從來不勸他去醫院。
燕知說難受不想動,幻象就會哄他好好睡。
因為燕知用來刻畫幻象的素材就是這樣的:他要什麼牧長覺都會給,他做什麼牧長覺都縱容。
而不是像現在正在開車的那一位,讓他覺得身上尖銳地疼了起來。
原本燕知覺得可以忍一忍的疼從骨頭縫裡鑽出來,酸液一樣地腐蝕著他的肌肉。
他的眼睛看不見,兩側的太陽穴像是各插了一根針,斷斷續續地通過跳躍的電流。
眼淚從眼角滑出來的時候,燕知覺得太誇張了。
他被撞裂肋骨的時候沒哭,胃疼得站不起來的時候沒哭,現在只是有點著涼居然值得他掉眼淚。
燕知在高燒中思考著過去為什麼沒有這麼難受。
有一次趕上大流感,燕知打了疫苗也沒能躲過去。
從學校坐車回出租屋的路上,他難受得站不住。
趕上夜間高峰,公交車上沒座位,燕知只能坐在車廂的台階上。
他旁邊坐著一位年輕的母親,在給一個小朋友講童話故事。
燕知聽了兩句,發現是《賣火柴的小女孩》。
這個故事在他很小的時候,牧長覺也給他講過。
「小女孩劃亮火柴,她看見了溫暖的火爐和香噴噴的烤雞……」
「……太冷了,她又劃亮第三支火柴。『外婆!』她驚喜地叫了出來……」
「為了不讓這一切消失,她點燃了手中所有的火柴……」
燕知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當時他是為自己慶幸的。
因為他不需要火柴。
他只要閉上眼,就可以把身邊冰冷的扶杆想像成溫柔的肩膀。
那個時候燕知也沒哭。
他甚至是幸福的。
牧長覺的車暖氣開得足,遠比充斥著流浪漢氣味的擁擠車廂要溫暖多了。
但是燕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一直流眼淚。
好在流眼淚沒聲音,他可以一直閉著眼睛假寐。
「到了,醒醒了。」牧長覺似乎相信了燕知在睡,輕輕揉了一下他的手,就從駕駛座下去了。
「嗯。」燕知假裝鼻音是因為剛睡醒的惺忪,趁著牧長覺下車把臉擦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