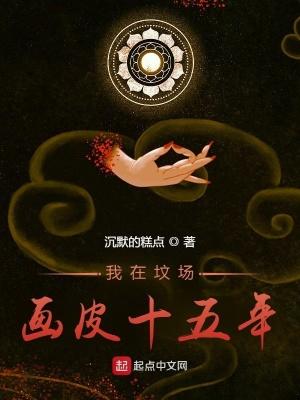凤阅居>东疆病长佩 > 第38頁(第1页)
第38頁(第1页)
眼見弓捷遠只在一旁立著,穀梁初道:「司尉不想活動活動?」
「屬下自小便懶,能不動彈就不動彈。」弓捷遠道,「況且手腳功夫實在不好,何必抖露出來丟人?」
「可是謙虛了嗎?」穀梁初問,「將門之子怎能身懶?不似武家風範。」
「我沒說謊。」弓捷遠神情十分認真,「不是每個兒子都像爹的。鎮東將軍戎馬倥傯弓劍俱佳,我卻生來孱弱,幼小時候十分難養,長到今天我爹吃了不少艱辛,如何還有力氣強我有好功夫?」
「可你六歲便在邊塞,」穀梁初說,「營房軍帳總是寒苦之地,不練功夫怎麼長大?十幾歲上又跟下將一起殺敵運糧,只是羸弱也撐不得。不想露了本事就說不想,何必搪塞本王?」
弓捷遠輕嘆一下,「王爺不信還有什麼辦法?你既統過兵的,也該知道不是每個軍伍中人都很強悍,總有一些人是沒有別的選擇,如我,也如一些沒有生路只為吃餉的人。」
穀梁初聞言淡淡一笑,「話都說到這個地步,孤王若再相強,未免不近人情。」
弓捷遠便不再說,只是遠眺莊門,盼著他的不系過來。
不系卻近中午方才出現,領它的人還是弓石。
弓捷遠接著一人一馬,略加詢問方知情由。卻是繼母無論如何不肯容人牽馬,即便王府僕從反覆解釋就是牽與弓捷遠用,繼母只怕上當受騙,堅持不允。那人無奈,且又機靈,回到王府央求弓石才能將馬領出。不系又是靈駒,只給認得之人牽韁,弓石也便跟著來了莊子。
「繼夫人真是將府的好主母。」穀梁初知道以後立刻贊道,「果然用心維護繼子繼女。」
弓捷遠不愛這種誇讚,臉色十分冷淡:「我們家裡不會當面喚她繼夫人,她也不會總是記得我們都是繼子繼女。」
穀梁初並不生氣,又點頭道:「你們如此,她便當真有福,何必計較丈夫心意?」
弓捷遠不想多說這些,轉身去摸不系。
不系異常漂亮。通體棕紅似緞沒有半根雜毛,深長雙眼如汪潭水,邊緣圈著漆黑墨線,瞳仁也是一對兒鋥亮的火睛,與其毛色相互呼應。
梁健看得艷羨,登時不練武了,湊到跟前嘖嘖地道:「這可真是一匹好馬。毛光腿長,尾巴如同仔細扎的大辮。看這肌肉條子,一縷縷的,必然耐跑。」
谷矯也過來看,他話少些,只說了句,「蹄子修得也細,雖然大如寶錠,卻也叫人想到女子玉足,精緻得緊。」
弓捷遠聞言看了看他,心道這悶傢伙眼光倒好,不系哪都出眾,四隻蹄子則最卓妙,不但蹄甲也是紅色,甲紋蹄路也很細膩,再加上蹄形圓潤趾瓣勻稱,實比尋常馬匹好看得多。
穀梁初自也懂得相馬,聽完兩人的話結論地道,「良駒難得,不是多金就能得的。司尉有幸,也定出自將軍一片愛子之心。」
弓捷遠訝於他的精明,點頭承認,「王爺睿智。不系並非中原品類,而是建州權貴跋山涉水地去西域買的,一路回來未及至家,便給我爹截住,追了五十多里方才搶來。這還虧得那些販馬之人不懂駕馭,否則便憑不系腳力,怎攆得上?」
穀梁初靜靜聽著,等著弓捷遠說完了話,方又問道:「如此說來司尉與它也必經過許多征服磨合,不系之名可是你給駒兒取的?」
「是我取的。」弓捷遠倒著回答他說,「我們磨合許久,卻無征服之說,不過彼此適應接納,相互交付而已。它名不系其實貨真價實——若不上陣廝殺處於極度緊張,卻是不用韁繩控制也能知道我的意思。王爺問問取馬之人,它在廄里可栓著嗎?」
穀梁初深知良駒不同凡馬之處便是靈性異常,當然就信弓捷遠的話,此時不由被他激起驅策之興,脫口說道:「如此佳物,孤王可能駕上一駕?」
「我勸王爺按捺,」弓捷遠立刻不樂意道,「不系難懂人間貴賤,只怕起了狂性摔著王爺貴體。」
「恁般孤傲?」穀梁初不甘心道,「怎地同你便不狂性遇到孤王便要摔人?你同它也不是打頭兒就認識的,還不是做了他的主子?」
「可我為了騎到它的背上和它一起睡了二十多天馬廄,日夜粘在一起,」弓捷遠哼道,「三餐都在食槽邊上。不系如今剛滿三歲,我遇到時還只是匹數月大的幼馬,它不認拴,更不要主,屬下千方百計才能得它認可,王爺尚是陌生之人,如何比得?」
「這樣說來除你之外別人乘不得它?」穀梁初微微有些不快,沉臉說道,「孤若只關著你,這好馬兒卻得閒悶到死?」
坐騎便在身旁,弓捷遠投鼠忌器,只怕惱了這人禍及心愛,見狀只好妥協地道:「也並不是全不能近,王爺定要坐它一坐,除非與我同乘,且得在我身前。」
穀梁初此刻生了少年心性,只要能乘便可,也不十分在意別的,當下便欣然道:「既是如此,司尉便就抱孤一抱,倒要親身感受感受它能跑得多快。」
弓捷遠聽了這話心中無奈,只得把臉貼貼馬頸,暗暗與它道歉。
不系與他分別數日,甚想念他,見狀也來回貼,似不在意別的事情。
幾人便在莊人引領之下繞出武場,來到一片遼曠甸子,弓捷遠先上了馬,縱著不系遠遠馳了一圈。
穀梁初原地望著他們,只覺馬靚人俏,就連弓捷遠那翻身而上的動作都是極致的賞心悅目,面上雖然仍無表情,心裡卻有一些暗喜:馬是好馬,人亦極佳。他們皆為本王所有。這便是權勢滔天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