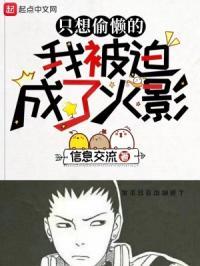凤阅居>大汉第一太子时槐序 > 第 107 章 番外七(第2页)
第 107 章 番外七(第2页)
刘彻一顿,他似乎听到了据儿声音。是他的错觉吗?
——父皇,你醒醒。
刘彻眼眸震颤,确实是据儿的声音,是他的据儿。
——父皇,你别吓我,你醒过来好不好。
刘彻四下逡巡:“据儿,是你吗?是你在叫朕对不对?据儿!”
——父皇,你已经昏睡多日,再不醒我要撑不住了。
——父皇,你不能有事。你答应过我的,会长长久久陪着我。
——父皇……
一声声呼唤传来,刘彻不自觉顺着声音寻找,忽然眼前似乎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意识再度模糊,重新睁开眼睛,人已经躺在温室殿的暖床之上,微微一动发现床旁趴着个熟睡的少年。
不是刘据又是谁?
刘彻大喜,颤颤巍巍伸出手,想要抚摸他,抱住他,却又不敢触碰。他怕这是一个梦,是他美好的幻想,一碰就会破碎。
因而他的手滞留在半空许久,最终垂了下来。
刘彻贪婪地注视着刘据,想着不碰便不碰,即便是幻象,能让他多看一会儿也好。
于是他就这样静静看着,恍然发现刘据面上满是疲惫,一双眼底全是乌青,也不知多久没有好好睡过了。
他的床旁还有张小塌,塌上有被褥床铺,似是陪睡之用。
刘彻正狐疑着,床旁身影蠕动。刘据微微蹙眉,脖子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默然对上刘彻的视线,腾一下起身,面露大喜:“父皇醒了!”
下一秒瞬间扑进刘彻怀里,泪水不受控制落下来:“父皇,你终于醒了。你差点吓死我了。父皇。”
怀中人的身体是温热的,熟悉的,连泪水也是。
不是梦,不是梦!
刘彻颤抖着坐起来,回抱住刘据:“是,父皇醒了,父皇回来了。”
他真的回来了。
()从大悲到大喜,刘彻又哭又笑,状似疯癫,情难自已,突然从喉头吐出一口鲜血。刘据唬了大跳,慌乱呐喊:“侍医,唤侍医。”
说着就要亲自去揪侍医过来,却被刘彻抓住手腕:“莫怕,父皇没事。不碍的,据儿别怕。”
又哭又笑,还吐了血,怎么可能没事。
刘据半分不信,急得跳脚。
刘彻却知道这应该是他梦中横亘在胸口的那口血,吐出来就好。他轻笑着再次将刘据拉入怀中,紧紧抱住:“据儿,你还在,你没事。真好,真好。”
刘据不明所以,察觉刘彻情绪不对,不想刺激他,便任由他抱着,顺着他的话回答:“对,父皇,我还在,我没事。”
甚至还伸手轻轻拍着他的背以示安抚。
直到侍医赶来,才将黏腻的父子俩分开。
太医署的人几乎全部出动,轮流把脉看诊一遍又一遍,得出结果:陛下已无大碍,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而今身体有些弱,需好生养养。
刘据终于松了口气,让人将消息传出去,令后宫与朝堂安心,却又吩咐暂且不必来见。这也是刘彻的意思。
刘彻拉着刘据在床旁坐下,细细询问:“朕昏迷多久?”
“十七日了。”
十七,正是他“梦”中所呆的时日。
“而今外面情况如何?”
“后宫有母后坐镇,大家都很安分。朝堂,我出面稳住群臣,让舅舅调遣兵马增援边关;又派去病表哥值守武库与骊山工坊,以防万一。索性,有火药的威望在,我朝内外,无人敢动。”
刘彻点头。帝王昏迷,若只是一两天还好。半个多月,极易引发朝局动荡,尤其可能导致别有用心的贼人勾连异族使坏。
刘据此番安排也是未雨绸缪,若真有意外,可随时策应,将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刘彻又问:“朝堂其他事宜呢?”
“我令众臣照旧上奏,由丞相整理后交予我,我暂代理。我若觉得可行的,直接批复。不确定的,我便请教丞相、太傅与舅舅。父皇可要看看?”
最后一句刘据有些犹豫,按理刘彻醒来,该向刘彻一一报备,但刘彻身体未痊愈,他恐事情繁杂,会让刘彻劳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