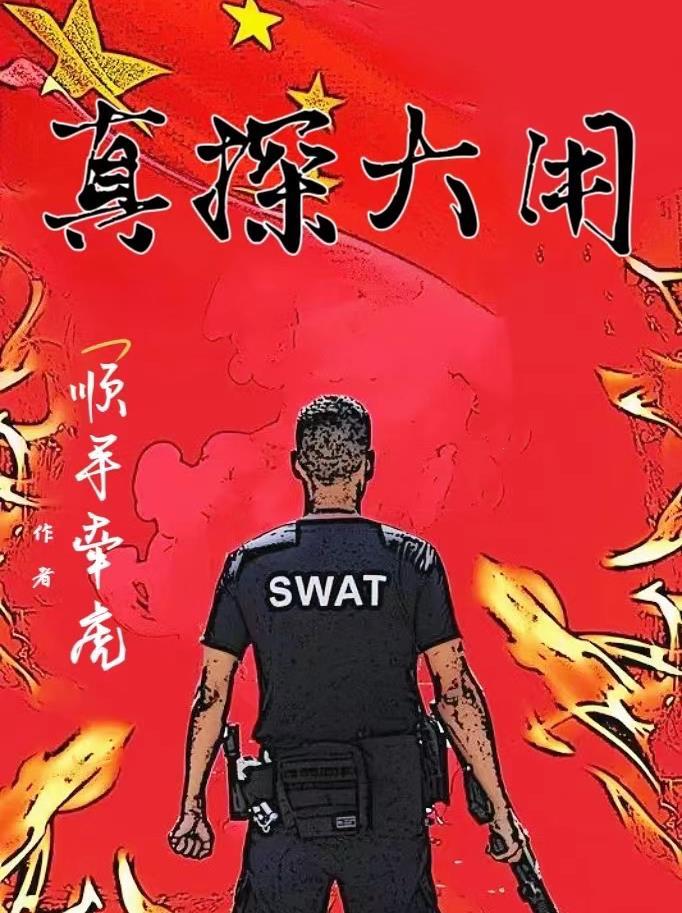凤阅居>一个妇女的日记全文在线阅读 > 第一百零五章 春怨(第1页)
第一百零五章 春怨(第1页)
一九九o年十二月十五日
回去大姐家里,只母亲和阿华在家。
晚饭前,我就放那盒沈借的录音磁带听歌。这只能给我更多的幻想更多的惆怅及对他的思念。
那《阿郎恋曲》“风潇潇的漫长路你只身飘零仍在寻觅你踪影杳杳像流星凄清清的秋雨点碰我窗前……”这张国栋唱过的歌,让我又想起他来,这是多么诱耳,象是张在唱着,但一看这录音带是沈的,应该想起他才是,这样,两个影儿就重叠在心上。
晚饭后去三姐家,在那里看电视,吃花生,感觉有好多话要说,却又说不出。
回时,路过卡拉ok舞厅时,柔柔的传来一歌,那是我熟悉的旋律:“想着他,想他那夜说的话,木棉花,怎能灿烂一季夏,觉我好傻,好傻。”
这忧伤的歌曲让我留步,感怀,伤情:“今夜好凄凉”歌声在我耳畔轻飘,渐渐的,它不再是从舞厅传来,它变成了隐隐的哀伤,沈的哀伤和我的哀伤。
他忧郁的眸子和他在一起时“共度这忧伤”的夜晚。
睡在床上,我失眠了。常常在回家休假的第一晚难以入睡。我在看“舞台与银幕”的报纸。看到徐小凤,张学友,童安格他们的行踪。觉得别人这样忙,自己这么无聊消极,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往日自己想死不活的生活又是什么人生?是我吗?娱乐圈的人都是忙人,艺术确实能把人提升到很高境界,把人带入一种不同凡响的世界,难怪我会迷上它。如什么《一生只爱一人》这流行歌曲年轻人都很喜欢,因为太对现代人的心境了:只愿一生爱一人。
“这是我一生的第一,虽然我在努力寻找自己,我却不能将你放弃,纵然你我只能短暂的相聚,允许我悄悄地思念你。”《一生第一》这歌让我更加喜欢它的歌词,因为它象一诗,也象我的心声,我想放弃文学追求音乐了,这样就不用知音难觅了,沈,张,严他们都很会唱歌弹吉他,才有了羡慕,他们都给我带来美的遐想,产生了爱慕。
艺术是清高的,让我无法不再爱它。也只有艺术,才把平平凡凡的人变成了不平凡的人,令人不得不佩服和羡慕。他们都让我有一丝的思念。难怪歌星影星有那么多崇拜者。
种种的爱恋,浮于心中,颇是难忘。直到凌晨两点钟才能入睡。若人在五山,是不会有这心境的。只有身处在不同的环境,才让人沉醉于这醉人的心境作美丽的浮想。
在家里的夜晚,才会让我这样留恋五山那些情。
九o年十二月十二日
早餐和妈一起吃瘦肉粥。
然后上街。去了阿君上班处。与她说在五山的烦恼:看别人成双成对,自己孤影一人,那种孤独很可怕,再且山沟很清静,很容易造成人的无聊和寂寞。见别人恋爱自己不能真是难耐。她说他们的门市部要迁去长垑,以后上班一点也不方便。
买了一盒录音磁带。挤在匆匆的人群中,不再感觉孤单,不再想恋爱,不再神秘,每个人都好平凡,一切都回到现实中,没什么美妙境界。
艺术的魅力,在这人与人的竟争,在金钱与物质的需要,又在现实的生存中逐渐消失了,他们吸引我的魅力,还是在现实中变弱,慢慢的消失。
我知道,我渴望追求的仍是精神上浪漫人生,但另一面却又不得不被现实屈服得“五体投地”。
正在这时,三姐和姐夫来了,我拿水果他们吃,姐夫说得更现实了,说:“千万不要在五山找男友。”
我说:“那孤独寂寞好难耐。”
姐夫说:“玩在一起是可以的,不要当真。”
三姐说:“我以前也是不容易过来的。”
我说:“你又不是打牌。”
姐夫就说:“那你不是比以前那帮人进步了,起码都可以借一些高娱乐的音乐文学艺术来打时间。写些散文什么的拿去韶关日报表嘛。”
三姐也这样说。
这时,我才知自己的日子过得好消沉了,对文学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对自己曾经的梦想也几乎泯灭了。他还说最好去学什么中文系,三姐就说去拿个成人高考的文凭。我听了心也热乎起来,我说五山的人才还是有的,就因为环境太山太静了,人的心也寂静,根本没有城里人的野心多。而所要学的东西都有太多的时间去学,但真的太寂寞了。
三姐还说乐昌很可能会展成“市”。
他们也都说得很现实了,情又值什么钱?现实的钱才最重要,韩燕曾说这样很俗气。姐夫说她一定会后悔她的选择。
处在这个小城市,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九o年十二月十三日阴
我的精神空虚,没有什么事让我满足自己的心灵。
回去家里也没什么可做,还不如一个人去逛街吧。去书店看看书或许是可以打掉时间的。
书店里也没什么我喜欢的书了,又去书摊上看,买了《舞台与银幕》琼瑶的《一帘幽梦》《青年文摘》总以为对书提不起兴趣了,然而却只有书才能使我感到快乐。
书,使我充实满足起来,那空洞洞无奈的心得救了,快活了,觉得自己所要的又都有了。
回家的路上,我才知,我渴求的精神粮食是胜过所有的一切,除开这,有人能救我吗?他能吗?不可能了。
不就是一本薄薄的书吗?怎么都可以令我满足?怎么说我是一个不安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