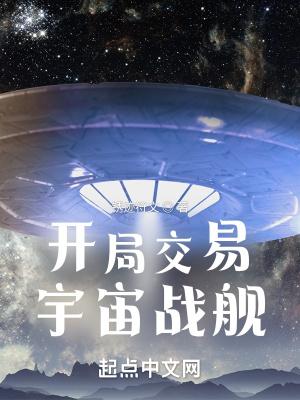凤阅居>许两世欢 > 第四章 布局 广结贤能(第1页)
第四章 布局 广结贤能(第1页)
桓之到嘴的话硬生生地哽在了喉咙,偷偷擦把冷汗,端起杯子,大口大口地喝起凉茶来。
逸公子看着桓之的样子,冷笑出声:“你该是紧张的,你娘亲是我姨母,我出了什么事,你一样逃不了。不过,我现在只是拿你这个花花公子当个幌子,还没有打算让你上刀山下油锅,倒也不必如此紧张。”
桓之尴尬一笑,忙道:“为王爷做事是在下的福分,王爷请尽管吩咐。”
逸公子站了起来,踱步到窗前,眺望着远方,久久地沉默着。
桓之早已明白自己的处境,舒将军在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其政见不合,而当今皇上也不是大度之人,一即位立刻把舒家配到了边疆。桓之不知道这个城府极深的王爷到底想干什么,但让他知道皇上的私密事,肯定是有拉拢之意。想来想去,他在心里打定了主意。
逸公子觉得给桓之考虑的时间已足够,缓缓转过身,看向桓之。桓之的面色平静,已全无紧张之色,坦然迎向了逸公子的目光。
逸公子很满意桓之的反应,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他手里太缺能人志士,而想成就大事,就必会用到手握兵权之人。
逸公子说:“东南那个占山为王的匪该剿了,近些年时有反意,朝廷很不放心。舒将军配到这里已有些时日,也该有点建树了。”
桓之心里迅盘算了一下,躬身回道:“这乌山的土匪不但在6地上为非作歹,这些年也没少在海上生事,家父早有此意,只是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最好能斩草除根,以免他们海上逃窜留下后患。”
血已经止住,逸公子将脖颈上被血染透的帕子塞入袖中,向门口走去:“那就先请舒将军拿出个章程来,怎么个从长计议法,讲明白些,对于我们的新皇帝来说也算个交代。”
“是,下官即刻告知家父。”
当晚,蓁蓁就搬到了后院。
红叶缠着妈妈问这问那,妈妈不胜其烦,随便搪塞了几句了事。红叶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恨恨地回了自己的房间。整个晚上,逸公子的样貌直在眼前晃悠,令她寝食难安。
在这个地方,红叶也算是见过不少男人了,真真假假也侍奉过几位有身份地位的老爷、公子,可逸公子在她的心里却是个特例。这样的男人,只消一眼,便让她丢了魂。红叶知道自己这是动了心,以她身份,犯忌讳是极其要不得的,可她却怎么也控制不住,甚至那晚的梦,都是逸公子在床边笑着望着她。
休息了没几日,妈妈便带了几位女先生去见蓁蓁。一位教书,一位教琴,一位教画,还有一位,妈妈没有介绍。
蓁蓁听着妈妈的介绍,向几位先生一一看过去,最后在中间站定,一本正经地福了一福给各位先生见了礼。妈妈留意着蓁蓁的样子总觉得这孩子心思深得惊人,也不敢多话,带着那位没有介绍的先生,便出去了。
“以前读过书吗?”
几位先生轮番上阵,一柱香的时间,便把蓁蓁脑子里的那点东西给摸清楚了。
妈妈命先生们给蓁蓁排了课时,蓁蓁倒也听话争气,认认真真地学着,只有在先生停下喝茶休息的时候,她的目光才转向门口,本是毫无表情的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若有似无的伤感,倘若碰到有人进来,她便又恢复到了平日里的样子,不喜、不悲、不怒,不哀。
这段期间,逸公子假借桓之之名派人送来了两个丫鬟,名唤香桔和甜樱,香桔年岁大些,人也稳重,话极少,但手脚颇为麻利;甜樱却是个跳脱的性子,许是不喜欢明月阁这种地方,一天到晚没个好脸色,话多嘴快做起事来也不尽人意,对蓁蓁这个小主人也不甚尊重。蓁蓁不气,也不和她计较,总之她房里的事也不多,更何况她也没资格选择身边人的去留,横竖不理她便是了。
又过些时日,逸公子托人送了好多东西,全是些闺阁女子喜欢的上等脂粉和簪花,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精巧小玩意,人,却一次都没出现过。蓁蓁极少动脂粉和簪花,倒是对那些鲁班锁、九连环和一些小机关之类的颇感兴趣,一得闲便拿出来把玩,没几天,她便请妈妈备了材料,开始学着做了起来。甜樱玩心大起,这事儿倒是积极,整日地盼着蓁蓁下课,一下课便拉她去柴房里做那些小活计。桓之见状便让妈妈找来一群工匠,将北边一个闲暇的屋子收拾了出来,备了各式各项的工具和材料,给蓁蓁修了间小作坊,自此之后,她在里面待的时日便更长了。只是,没人知道她要做什么,有时她能做出一两个眼睛会转嘴巴能张开的小猫小狗,有时是一堆让人看不懂的废铜烂铁和废木头。再之后,她又多了一位男先生,专门教她做那些手工,至此,她再做出来的东西便有了章法,慢慢的,竟然能做出像飞针一样的暗器出来。
远在千里之外的逸王府内张灯结彩,到处挂着红绸。为了边关安宁,皇帝答应祁国和亲,而祁国那边竟不顾逸公子还在三年孝期,非要将婚事定在明日。说起来这也是场孽缘,新皇登基祁国国王携王子公主前来觐见,公主对主持大典的渊逸王爷一见钟情,几次派使臣游说全被他以孝期为名给挡了回去。如今新皇根基未稳,祁国蠢蠢欲动,几次挑衅,为了百姓的安宁,新皇将在外私访的渊逸召回,逼他应下了这门亲事。
渊逸年方二十,还未册封王爷的时候纳了两房侧妃,此次迎娶祁国公主用的王妃的礼制,自是声势浩大。
舒将军领兵不便进京,便遣了舒桓之代为祝贺。桓之带来了边疆的消息,自然也有蓁蓁的。
渊逸耳中听着桓之讲述着关于蓁蓁的种种,手里拿的是她做的暗器。暗器是为铁铸,绑在手腕的束带为皮质,触手冰凉,就像她的手一样。他久久未出声,看似在研究暗器,实则心绪早已不知道飞到何处。
“听话吗?”渊逸突然问。
“自是听话的,学东西也快,您说得没错,她的确是个极聪明的,这几个月把那些女先生的本领学得八九不离十了。”
“那就换一批,只要她想学。”
“是。”
“脸瞧着生动些了吗?”
桓之想了想:“比起刚来的时候是好些,不过比起寻常女子还是一眼就能瞧出不同来,话也极少。”
“这性子是有些不同寻常,无畏无惧才能狠绝,心无旁骛方可将劲儿使到一出,不然哪能学东西这么快,这要是个男人,状元郎都不在话下,可惜是个女儿身。”
“说是女儿身,但她喜欢的东西却都是些男人们爱玩的,舞刀弄枪做暗器自不必说,整日里仍旧素白的一身衣,不束更不用说用胭脂水粉,偶尔妈妈说她一句,她便一副懵懂的样子,我瞧着她不是听不懂,是装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