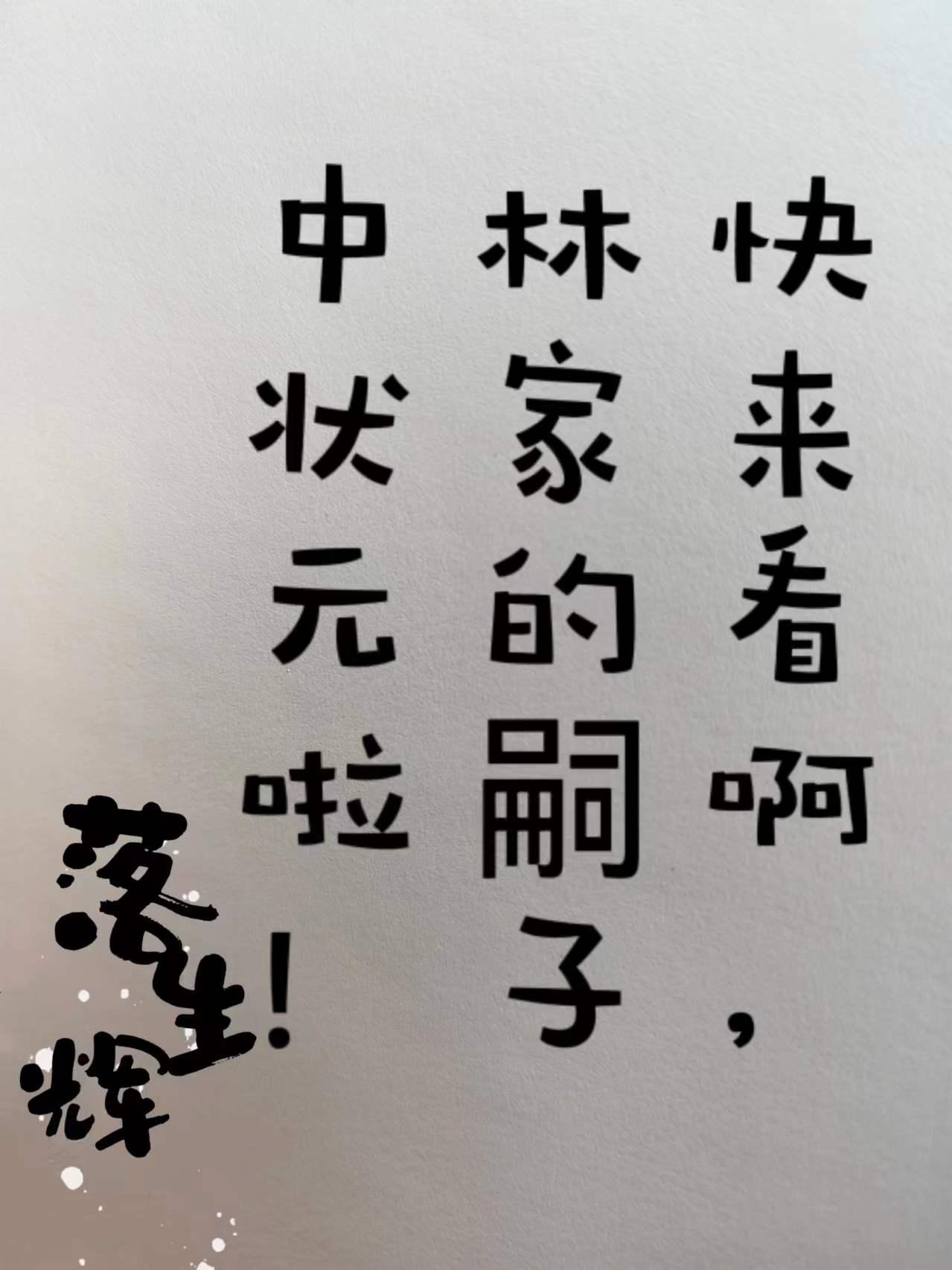凤阅居>初看红楼 > 第二十章 还泪还尿(第2页)
第二十章 还泪还尿(第2页)
“真是个怪人”,晴雯望着冷水寒离去的背影,嘀咕道。
……
冷水寒离开绛云轩后,来到荣禧堂。
方才接旨时,政老爷一副大祸临头的模样,想来其中有他不知晓的门道。不妨问问看,心里也好有个底儿。
贾政正在书案前奋笔疾书,瞧见詹光进来,问道何事,詹光说冷水寒来了,在外堂侯着。
贾政听了,并未起身,继续将书信写完,吩咐詹光去趟王府,把信函交给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随后,贾政来到外堂。
道了两句不冷不热的喜,贾政便问:“你有何事?”
冷水寒也不拐弯抹角,开诚布公道:“政老爷平日里,对我照顾有加,若是老圣人这封敕旨,给贾府带来难处,还请政老爷直言。”
贾政闻言,抿了两口茶,神色平静下来,将朝堂上新党之事,昌明派、隆盛派、骑墙派盘根错节的状况,前前后后讲述了一番。
接着又叹道:“老圣人的隆恩,看似鲜花着锦,实则烈火烹油啊。”
“政老爷是隆盛派?”,冷水寒问。
“我把元春送进宫里,给隆盛帝做女吏,你说,我是哪一派?”,贾政苦笑道。
“老圣人早晚会驾鹤西去,贾府为将来考虑,站在隆盛帝这边。你如今却得到老圣人赏识,你叫我如何是好,叫元春如何是好,隆盛帝必然会对她心生间隙啊!”
“政老爷觉得,老圣人傻吗?”,冷水寒又问。
“可不敢妄言!”,贾政忙道。
“政老爷认为,老圣人是想借我之名,再次推行新法。可第一次推行新法,老圣人就吃了大亏,废太子不说,还禅让了皇位。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圣人会傻到再次推行新法?”
“这次可没人给他挡刀!”,冷水寒思索片刻,说道。
“那老圣人,为何要封你‘义忠仆’?”,贾政面露疑惑之色,反问道。
“政老爷先前说,第一次推行新法失败后,新党魁黄阁老被凌迟,新党就此势弱。旧党从而顺利推举隆盛帝登基。既然新党已经势弱,那为何老圣人还能把持朝政,隆盛帝只有听训的份?”
冷水寒以问代答,继续问道。
“这……”,贾政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他想不明白。
“恕我直言,大齐开国已经有百余年,王公勋贵多是武将之后,只知贪图享乐,一代不如一代。比如政老爷你,贵为国公门第,却只落得个区区工部员外郎,那理国公之孙柳芳,也只是步军统领衙门里一总兵,连统领都没捞上。”
“依我看,旧党势大,不过是爵位唬人,纵然有高品,也都是些闲职。新党势弱,无非是韬光养晦,隐而不。通过科举一途,入仕的寒门子弟,虽然无爵,比如那刑部杨侍郎、都察使王永吉,却都是朝堂运转的实权文官。”
“只有这些实权文官,对隆盛帝阳奉阴违,老圣人才能继续把持朝政。与其说是老圣人要推新法,不如说是新党挟裹了老圣人,要推行新法。”
“啊?”,贾政大为震惊,失声道。
“我想,新党不仅要推行新法,还要换新天。他们既然能够容忍旧党推选隆盛帝登基,必然认定这是个傀儡皇帝,不值得一争。”
“贤侄的意思是,新党已成燎原之势,贾府也要改换门庭?”,贾政神色愈惊慌,对冷水寒的称谓,都改成了贤侄。
“不”,冷水寒摇了摇头,正色道:”政老爷把女儿都送给了隆盛帝,还是个国公世家,便是倒向新党,也是新党里的异类。”
“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冷水寒顿了顿,接着道:“政老爷大可修书一封,送入宫中,交给贾女吏,说我冷水寒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和贾府一样,都愿为隆盛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番得老圣人隆恩,也是无奈之举,只为卧底新党。”
“你这一面之词,纵使我女儿信了,隆盛帝如何肯信?”,贾政不由得气问道,伸手拍响了桌子。
“交个投名状便是”,冷水寒淡淡道,心里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哪来的劳什子新法!
什么摊丁入亩、什么火耗归公、什么一体纳役,全是照搬雍正时期的改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无费工夫。
那操控新党的人,就是潜伏在暗处的穿越者!
放那场火的人,指使吴德毒害贾雨村的人,伪装成天家内斗的人,我倒要看看,在我真老六面前,你个假老六,还能躲到何时?!
不过,新党的新法,毕竟有利于民,倘若我与新党为敌,这样一来,我岂不是反派?
等等,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冷水寒又是一番暗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