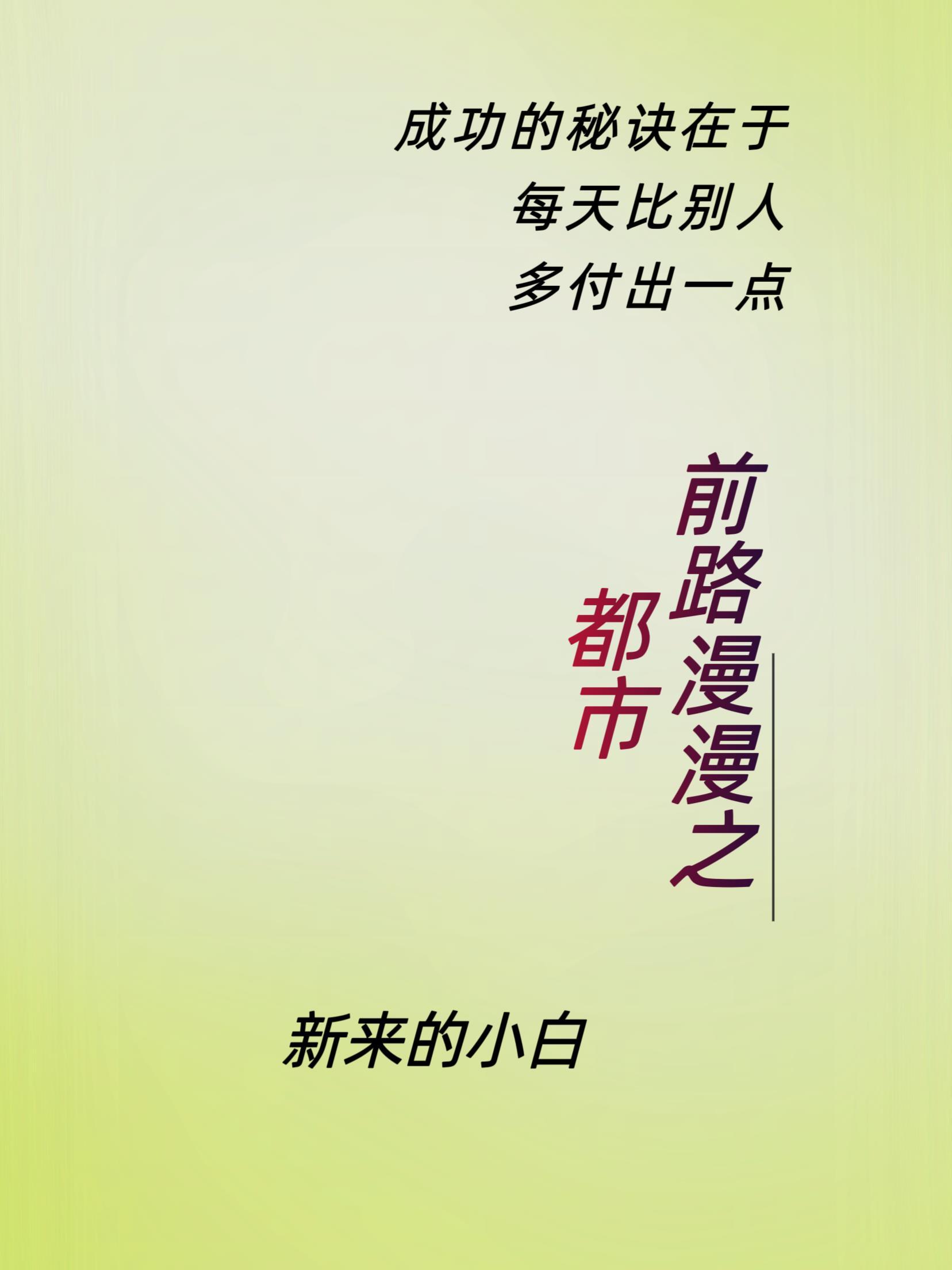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向他坠落免费阅读全文无弹窗 > 第43頁(第2页)
第43頁(第2页)
「白副官……老郭在家,你有事就叫他。」
軍醫這兩天有事回老家了,要看大夫還得現找。警衛知道這事輪不到自己來操心,但出於禮貌和關懷還是模稜兩可地囑咐了一句。
「好,謝謝。」白項英過了院門停下腳步,「今鴻沒回來過吧?」
「小霍?他昨天好像有事找你,問了一晚上,今早跑去司令部了。」
「沒回學校?」
「學校今天臨時放假。」
白項英知道霍今鴻跟警衛撒了謊,但沒有多說什麼。他早有預感對方不肯乖乖待在學校,依他那性子心裡藏不住事,定會打破砂鍋問到底。正好霍岩山這兩天不在家,再怎麼逃課都沒人管他。
當然,逃課是其次,他知道他為什麼回來。
「今鴻回來要是想見我,就說我在休息。」
「是。」警衛聽出他的疲憊,「白副官你休息去吧,一會兒我讓老郭去看住他,不讓他打擾你。」
。
白項英打開水龍頭,背對鏡子一點點脫掉上衣。
西裝外套扔在地上。那是齊繼堯的東西,美其名曰替他遮羞——襯衫扣子掉了,鮮的鞭痕從領子裡冒出來,嘴角也腫得厲害。
臨走時那人對他說:「告訴霍岩山,我很滿意。」
送他回去的是齊繼堯的私家車,司機從反光鏡里看到他的臉,多嘴問了句:「先生,您不要緊吧?」
白項英笑了笑說沒事,抬手把外套領子拉高了些。
——要緊,又能怎麼樣呢?
外面天氣很好,太陽光射進來,讓他想起昨晚臥室上方的那盞水晶吊燈。那時候他沒能昏死過去,現在卻在延綿的顛簸下有了些許睡意。
他猶豫是否要讓司機中途改道,隨便找家旅館或者煙室之類的地方。不能就這麼回去,不能用這副樣子去見宅子裡的警衛和勤務兵——連陌生司機見了都要問一句「要不要緊」的地步。
汽車一路開出市區進了膠縣。白項英最後還是什麼都沒有說。他太累了,到了旅館不知道還有沒有力氣自己回去,況且也不敢自作主張改變行程。
——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都已經到了極限,他再也經不起哪怕一點點額外的懲罰了。
浴缸里蓄滿了溫水,白項英蜷著腰脫掉褲子,兩條腿不住地打顫。
長時間沒有進食導致的低血糖,又或許是藥物留下的副作用,令他虛弱到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費了好大的勁才跨進浴缸,小心翼翼地屈腿蹲下,溫水漫過胸口。
身上那些本來已經麻木的傷口一下子全部復甦了,疼痛像網一樣將他束縛住,勒緊他。
這是霍岩山專門給他用來洗澡的地方,平常除了自己沒人會進來。白項英忍痛仰躺下去,讓水完全沒過肩膀——這具破碎不堪的身體,哪怕短短几秒也不該暴露在燈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