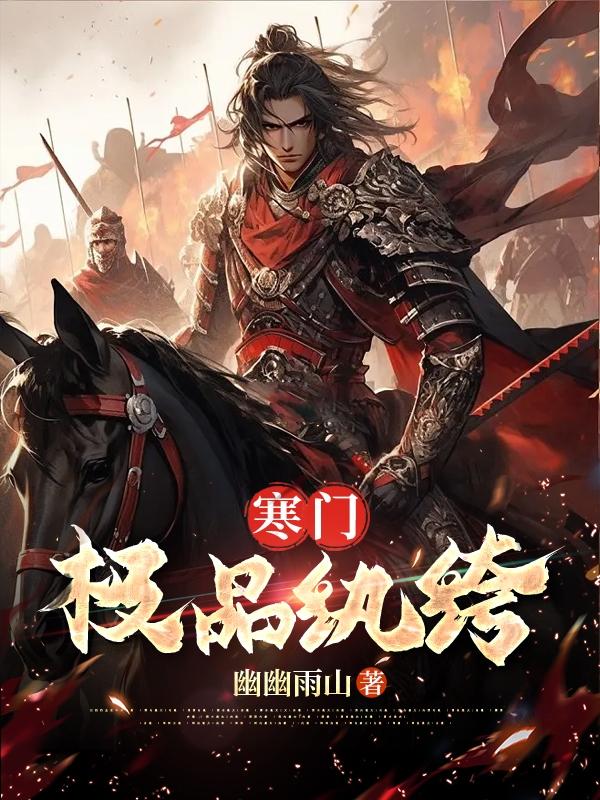凤阅居>奈何明月照沟渠的全诗 > 第4章(第3页)
第4章(第3页)
既这么着,话已出口,也不往回收。
“你不必有什么负担,我也是因今儿个的事太着急了,吓到你了吧?其实你的情况,和徐家那孩子倒有几分相像。”
徐家那孩子,说的是徐稚柳。
徐稚柳虽与徐忠同宗同源,但只是徐忠的远房侄子,不是亲生,之所以担着“少东家”的名号,全是徐忠的算计。
这在景德镇不算秘密,大家伙都知道,徐忠为人刻薄,命里无子,只有一女。
多年以来为传宗接代一事他可谓愁断肝肠,奈何妻早早过世,几房小妾也不争气,折腾十数年,竟然颗粒无收。
到头来还要靠唯一的女儿招婿。
“我看那老头早有把女儿嫁给徐稚柳的打算,说什么亲上加亲,心里打的什么算盘,谁不知道?得亏徐稚柳有情有义,若承了那老头的情,窑口有人传承,且觅得良妻,也算两全其美。”
他们两家虽然互为对手,但有一说一,徐稚柳当真是景德镇这一辈里最拔尖的存在,可以说十年以来,无出其右。
王瑜打打心眼里欣赏他,也欣赏他和梁佩秋相似的际遇背后相似的情义。
“你是不知道,当年他家道中落,前来投奔徐忠时,湖田窑正在闹分家。徐忠那个性子向来霸道,不听劝,还用人唯亲,湖田窑传到他手上就那么几年,攒下一堆陈年积弊,宗族关系冗杂,几乎要把湖田窑的血吸干。等他现里头根子开始烂,想要清理,却没本事,就在这个时候徐稚柳来了。”
十年间徐稚柳不仅将宗族势力牢牢抓在手中,更提拔了不少族内后生,为避免他们同自己一样因家境问题被迫弃学,还在家乡修筑学堂,资助学子。
其青云之志一望而知。
可他至今不曾离开湖田窑,显然认命了,封侯拜相已是昨日黄花。徐忠若能搞到这么个女婿,那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不过他也不亏,若能娶到佩秋这么个儿媳妇,也算他祖上积德。
说一千道一万的,总归一个,谁让王云仙埋汰呢!
王瑜是个实诚人,说话也实在:“云仙确实方方面面都差了些,配不上你,只你放心,只要我一日在,必不能让他委屈了你,我也不会亏待你……佩秋,这不是小事,你不要着急,细想想再给我答复。”
他不想挟恩以报,再三道:“佩秋,家里的情况你知道,今儿湖田窑的情况大家伙都看在眼里,细想想谁不后怕?若非徐稚柳一力顶着,我安庆窑此刻尚能安宁否?我呢,居安思危,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虽然有些突然,但你相信师父,这个念头我曾经想过很多次,并非一时兴起。”
他这么说完,眼神恳切地望着她。
梁佩秋这才现他鬓角生出了许多白,不知是什么时候的事,好像昨儿还没有,今儿就有了。
以前听窑口的老人说,人老就是一瞬间的事,原还不觉得,现下亲眼看到了,一时不知滋味。
她微低下头去,看脚下的落雪。
过了不知多久,她才开口:“师父,让我想想吧。”
送王瑜回房后,梁佩秋独自一人回到位处安庆窑西角的厢房。
此时夜已深了,位处王家宅院的西角乌漆嘛黑,没有半点声响。
王云仙曾不止一次抱怨她住得偏僻,想给她换个院子,她不肯,王瑜以为这是她身为女子的顾虑,自然多有照拂,非但一力摁下王云仙的念头,平日也不许人过来打扰。
时间一长,大家便也忘了这西角临江,后头有一面墙。
墙后是狮子弄。
梁佩秋进了屋,将门合上,点上蜡烛,捧着杯沿有一口没一口地吮着凉水,不知想着什么。
静坐半晌后,她忽然推开内窗一跃而下,朝着西角后墙跑去。
墙角有一棵百年梨树,树干遒劲有力,分支奇多,远远看去像一蓬炸开的云。
在月光笼罩下,那蓬蓬撑开的云好比一间树屋,潜藏着少女所有不为人知的过去。
梁佩秋熟门熟路地爬上树,寻到舒适姿势,窝进枝丫,攀着嫩白的花蕊,伸长脖子向狮子弄看去。
过了一会儿,远处渐有脚步声传来。
轻轻地,落在她心上。
于是一整晚的恍惚、不安和不甘,都在此刻落定。
想着王瑜带回的消息,如她所料,他果真没有和安十九狼狈为奸,她很高兴,为他高兴,也为自己的笃定而高兴。
他还是曾经那个意气风的少年。
可是,他为什么要对人甩脸色?他在做给谁看?
师父只是旁观者,尚且自乱阵脚,想替王云仙求娶她以顾全安庆窑的将来,那么他呢?
他被推到那风口浪尖去,又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