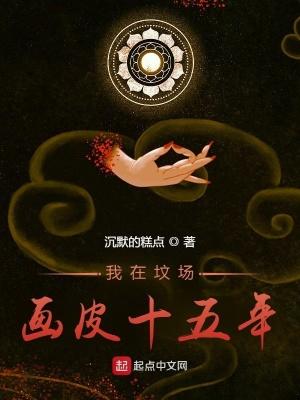凤阅居>被迫嫁给丑夫后申玟结局 > 第62頁(第1页)
第62頁(第1页)
說著,她問她兒子道:「前幾天我不是讓你把家裡那四十畝地找人租出去嗎,咋樣了?」
王合麼不太耐煩,「問過了,沒人租。」
聞言,老王太太納悶道:「怎麼會沒人租呢,咱要的租金也不高啊。」
王合麼不吭聲,他那些喝酒的朋友偷偷告訴過他,村里人都不敢租他的地,怕他秋收時鬧事,到時候白忙活一年。
老王太太犯了難,說:「要麼再去跟那個醜八怪要點錢去,那地就算是自己種,也得有錢買種子和肥料啊。」
王合麼臉色一下子沉下去,罵道:「那個狗娘養的,我上次去找他,他說以後一分錢都不會再給我,」他咬牙切齒道,「等著,早晚有一天我讓他好看!」
晚飯上只有發霉的高粱米飯和一盤子炒野菜和一碟子鹹菜,沒有肉,更沒有酒,王合麼越吃心情越差。
吃完飯,他沒錢再去賭場了,就在村子裡瞎逛,聽見誰家玩牌呢,就往人家進。
進去也就是干看著,手癢得不行,可口袋裡溜空。
打牌時有人喝酒,他饞蟲犯了,厚著臉皮跟人蹭了半壺酒喝。
他日日飲酒,酒量沒升反降,半壺就把他喝得里倒歪斜。
主家媳婦瞪了他好幾眼,那家男人見了媳婦眼色,推了紙牌,說:「天晚了,不玩了不玩了。」
王合麼從那家出來了,無處可去,站街上發愣,過了會,他才反應過來,身後那家一直沒人出來,打牌的笑鬧聲又起來了,合著就把他給變相攆了出來。
王合麼罵了一聲,嗖嗖往家走,家裡不捨得點油燈,都睡下了。
他進了外屋,摸索著找到菜刀,就又出去了。
又回到那家人門外,聽著裡面說話玩牌的聲音,他牙根咬得死緊,就要衝進去給他們顏色瞧瞧,可都已經進了院子,到了屋門口了,他又退縮了。
裡面起碼有四五個男的,他肯定打不過。
王合麼憋屈地出了那院子,焦慮地在街上來回亂走,走著走著,他臉上露出發狠的表情,拎著菜刀在嗓子眼裡罵道:「你不讓我好過,我也不讓你好過,不給我錢,我現在就去你家把你弄死!」
他念叨著狠話,往村子西邊疾走,醉得渾濁的腦子已經開始幻想那個醜八怪死了以後,房子、鋪子還有地都得歸他。
還有那個嫁進來的小哥兒,長得比地里發芽的小蔥還嫩,到時候他也一併接手,看他不把那小美人兒操到天天下不來床!
村子一共也沒有多大,走了不到一炷香的時間,王合麼就到地方了。
周圍黑漆漆的,沒有人,只零星一兩戶人家還亮著油燈。
王合麼特意墊腳往院子裡看了看,見裡面窗子都是黑的,頓時膽子更大了。
他試圖悄悄從院牆翻進去,但牆比他個頭還高,而且他醉得腳步虛浮,試了好幾次都沒上去。
王合麼懊惱地用頭撞牆,撞了兩下,疼痛讓他短暫地振作了一會,他立刻又一次嘗試,這次終於費了好大勁爬到了牆上。
可他剛邁了一條腿過去,就見牆底下一雙發光的眼睛正盯著他。
王合麼一聲驚叫悶在了嗓子裡,狗叫聲驚雷一般響起,那雙發光發亮的眼睛跳起,他只覺得腳上猛烈地一痛,不由自主就往牆外倒去,哐啷一聲摔在地上,疼得他兩眼發黑,好在咬他腳的那隻惡犬也被迫脫了口。
院子裡,有開門的聲音傳出來,一個低沉冰冷的聲音問道:「誰?」
王合麼捂著嘴,嚇得臉色發白,撿起掉在地上的菜刀,忍著疼拖著腳一路往自家的方向逃去。
院門內,邱鶴年目光在院子裡各處一一掃過,見沒人答應,他往院門處走來。
雞窩裡的小雞醒了,在不安地鳴叫。
「二喜!」邱鶴年制止還在朝外面狂吠的黃狗,二喜就聽話地不再叫,只用狗腦袋去蹭他的手,那些雞也跟著安靜下來。
邱鶴年安撫地摸了摸二喜的頭,打開院門往外看,外面路上靜悄悄,空無一人。
今晚沒月亮,天太黑,看不清地上的痕跡。
他在門口又站了一陣,見還是沒有異常,這才栓上院門,去外屋給二喜找了塊剩的骨頭餵給它。
回了屋,他把屋門也鎖好,又把手洗了洗,擦乾淨,才回裡屋。
裡屋沒點燈,但邱鶴年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大概都看得清。
床帳放著,隔著床里的人。
年輕小哥兒的聲音輕輕的、柔柔的問道:「二喜在叫什麼,外面怎麼了?」
邱鶴年褪去外袍,放置在一旁的椅子上,回應道:「沒事,可能是野貓。」
「劉獵戶這次探親要走多久啊,我想二喜多在咱家待幾天。」那哥兒說。
邱鶴年彎腰脫鞋子,說:「這陣子他不上山,你喜歡就讓二喜多待幾天,等他回來我去跟他說。」
「你要是想養狗,小莊家大狗快下崽了,到時我去替你要一隻。」邱鶴年直起身,撩開了床帳。
黑暗中,床上影影綽綽的人影擺出的姿勢,讓他抓著床帳的手不由自主握緊,喉結微微滑動,雙眼眯了起來。
清言朝他撒嬌,「你好慢。」
「嗯。」邱鶴年聲音沉到沙啞,他抬腿上了床,手裡的床帳落了下來。
一個吻也同時落下,清言抬起小巧的下巴,迎了上去,在親吻間他含含糊糊地抱怨,「手好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