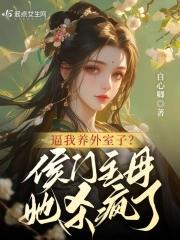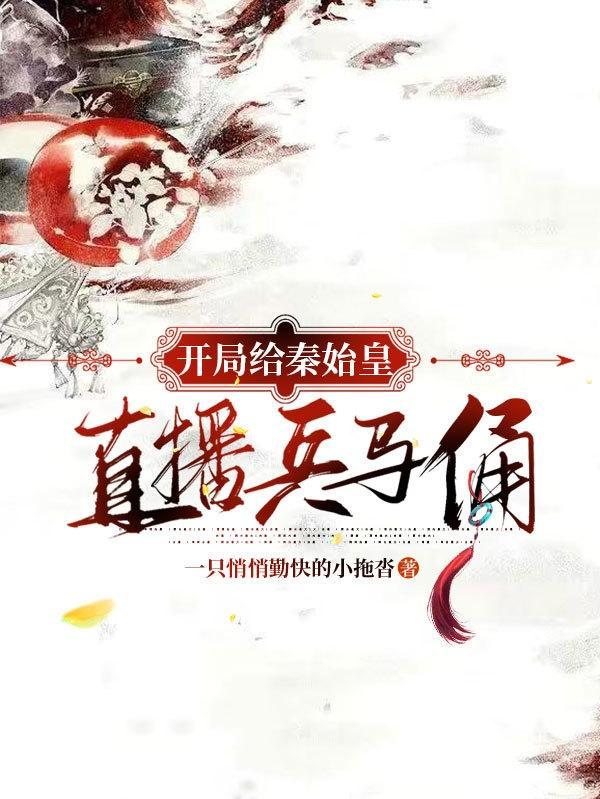凤阅居>罗伯特麦基虚构艺术三部曲是不是对应三本 > PART 3 人物宇宙(第6页)
PART 3 人物宇宙(第6页)
任何类型都可以变成动画。
8。自传
任何类型都可以将一个回忆录的主人公戏剧化。
9。传记
任何“命运情节”都可以将一个传记主体的外在生活装载在
它的中心。然后作者便可以决定是否还要利用一个“性格情节”来刻画只有他才能想象的内在生活。唐·德里罗讲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的《天秤座》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讲述玛丽莲·梦露的《金发女郎》则对其主体采用了“退化情节”的变化弧光。
10。高艺术
“高艺术”是常见于艺术电影、实验戏剧和先锋流行小说的一种表现主义风格。这些作品是从一个主类型开始,然后将其人物推向各种碎片化的偶发事件,以其不可靠的视点在不连贯的时间框架中进行讲述。在这种宏观畸变中,它们通常还会加入混合媒介、超验影像和图形符号的微观处理。
类型杂糅
当一部作品的中心情节和(诸多)次情节杂糅了各种不同的类型时,人物复杂性便会自然而然地轻易拓展。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一个“犯罪故事”的中心情节辅之以一个“爱情故事”的次情节,便能本能地将一个侦探主人公的内在生活拉向警务工作所要求的强悍素质以及浪漫情缘所需要的温柔感觉。
类型可以混杂,也可以融合。
混杂类型将两条或更多的故事线交织在一起。其相反相成的情节主题能丰富作品的总体意义,同时还能增添人物的界面和维度。
例如,大卫·米歇尔的小说《云图》就是将发生在六个不同时间和背景中的六个不同类型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教育情节”
“幻灭情节”“进化情节”“政治剧”,以及两个“犯罪”次类型——“惊悚”和“监狱剧”。从一个纪元到一个纪元,从一个故事到一个故事,所有六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都能互相呼应。
即如作者在BBC广播四台的一个访谈中所言:“主要人物,除了一个,都是同一个灵魂在不同躯体内的转世投胎,以一个胎记作为识别标志,贯穿了整部小说。(《云图》的)主题就是弱肉强食——个体捕食个体,群体捕食群体,部落捕食部落,民族捕食民族……(我)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也体现了这一主题。”
混杂设计会使作家必须掌握以及读者观众将会预期的类型常规的数量倍增,与此同时,它们还会在数量和种类上扩充作品的卡司。像《云图》那样庞大的卡司群体便对作者提出了各种极高的创作要求。有些读者会在页边空白处做笔记来厘清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
融合类型是将情节线进行杂糅,用故事套故事的办法来阐明动机并增加其复杂性。
两个例证:
拉塞尔·哈博的《爱无止境》的总体类型是“家庭剧”,属于“命运情节”之一种。一个已然麻烦不断的家庭由于父亲去世更是雪上加霜,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戏剧问题:未亡人及其两个儿子是会继续作为一个家庭而团结如初,还是会分道扬镳?
不过,这一问题的答案却取决于在
每一个主要人物心中运行的三个故事的变化弧光:未亡人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进化情节”追踪着她两个儿子走向成年的斗争过程。换言之,这三个内在的故事线激励了“家庭剧”的高潮:这个家庭之所以得以保全,是因为他们的人性进化,令其发现爱无止境。
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是类型融合与类型混杂二者兼备。演员里克·道尔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和特技替身克里夫·布思(布拉德·皮特饰)之间的“密友情节”与一个“进化情节”相融合,以道尔顿的内心变化为弧光。道尔顿要努力找到内在力量来克服他的酒瘾并挽救他的演艺生涯,但他与布思之间互相依存的友谊却堵住了他的自我控制之路。这两条故事线之间的冲突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戏剧问题:这两个男人是会为了道尔顿的未来而牺牲他们的友谊,还是会继续作为朋友而一醉方休,直到最后的悲惨结局?与此同时,一个生死攸关的“犯罪情节”还与这两个融合故事交相辉映,并以臭名昭著的曼森帮的入室侵犯作为所有三个故事的高潮。
当类型融合时,一个故事的走向决定另一个故事的结局。这种杂糅缩减了卡司的规模(一个人物扮演两个类型的主人公),同时还减少了类型常规的数量(当一对恋人在一起银行抢劫案中见面时,一个激励事件便启
动了两个类型)。
第十五章
行动人物
每一个人物都有其自我故事。这便是她回顾自己的各种过去身份时、反思自己的现在状态时、展望自己的未来自我时对她自己讲述的三个故事。她的未来故事会变得最为重要,因为它将构建并统领你的作品的进程。
在其童年的某个时段,当她沉浸在自己的家庭养育、学校教育和总体文化时,她一定有过一种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理想的身份、理想的爱人、理想的事业、理想的生活方式——事情应该发生在她身上的方式。随着时间推移,她会不断改写自己的过去,使之更加合乎理性,为她是如何变成她现在已经变成的样子提供理由。当她自问“我是谁?何至于此?我如何才能融入这个世界?”时,她的自我故事便能给她答案,将其诸多自我拉拽为一个统一体。[1]一旦付诸行动,她的自我故事便能给她一个非她莫属的“作案手法”(借用“犯罪类型”的一个术语,下文简称“作法”),一种独一无二的行事方法。
一个人物的“作法”会超越创造其人格的各种人物塑造特性的集合——声音、身姿、手势、衣着、情调。会赋予她一个招数模型,令其习惯性地用来追求其欲望目标,身体力行地奔向其理想未来。她那非她莫属的“作法”会引领她努力处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不测事件——她打
算如何着手去得到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外加她计划如何逃离她害怕的东西。在整个人生过程中,一个人物可能会放弃她年轻时候的“作法”,但在更多情况下,仅仅是根据家庭压力、工作压力,当然还有爱的压力进行调整而已。[2]
当你的故事的激励事件颠覆了你的主人公的生活平衡时,她会试图将自己的自我故事强加给阻遏其意志和欲望的各种力量,以恢复平衡。换言之,她会一意孤行,以其独一无二的“作法”来应对。所以,若要将你的人物付诸行动,首先就必须炮制出她的自我故事,然后想象出她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样子,并锁定其特有的“作法”以实现那个未来。
人物的各种“作法”往往会麇集于各种不同的主题。为了给你一个可能性的指南,我罗列了三个最常见的前提,并辅之以从戏剧、连续剧、小说和电影中摘取的案例。每一种案例我都附加了一个有可能推进故事的额外的反转。
好莱坞主题
许多人都想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过得跟电影似的。他们会在最喜欢的故事中找寻自己的个人目标;然后把自己与故事人物等同起来,并把其虚构行为作为定制其真实生活“作法”的模板。作家会将这些行为回收进故事之中,结果是,特定的“作法”对事实和虚构,对真人和虚拟人物都有驱动作用。以下仅仅是五种:
神秘恋
人
由于主人公觉得日常生活太乏味,其“作法”便是去追寻一个神秘莫测的恋人。
案例:希区柯克的《迷魂记》中的斯科蒂·弗格森、保罗·塞洛克斯的小说《一只死手》中的杰里、苏珊·希尔史蒂芬·马拉特拉特的戏剧《黑衣女人》中的阿瑟、大卫·林奇的电视连续剧《双峰》中的戴尔·库珀。
反转:最终的结果是,这个神秘人物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隐藏或言说的。为了吸引恋人,她只不过是在假装深不可测而已。
另类探险者
主人公感觉跟正常社会格格不入,于是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奇特的自我版本并追寻跟她一样怪异甚至比她还要怪异的他人——越另类越兴奋。
案例:帕姆·休斯顿的短篇小说集《牛仔是我的证人》中的无名解说人、爱德华·阿尔比的戏剧《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中的马丁、南希·奥利弗的电影剧本《拉斯和真女孩》中的拉斯、拉里·大卫杰里·森菲尔德的情景喜剧《宋飞正传》中的科斯莫·克莱默。
反转:我们常常以为惊世骇俗的外表后面会藏着一个令人痴迷的人格,可是主人公却发现其伴侣的文身、疤痕和彩条发型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徒劳噱头而已。
童话故事
主人公扮演一个童话故事王子或公主。
案例: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燕草露夫人》中的哈德威克-摩尔太太、罗纳德·摩尔的连续剧《古战场传奇》中的克莱尔
、桐华的小说《步步惊心》里的张晓、威廉·戈德曼的电影剧本《公主新娘》里的芭特卡普。
反转:当王子变成小丑,公主变成女巫时,童话世界便成了荒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