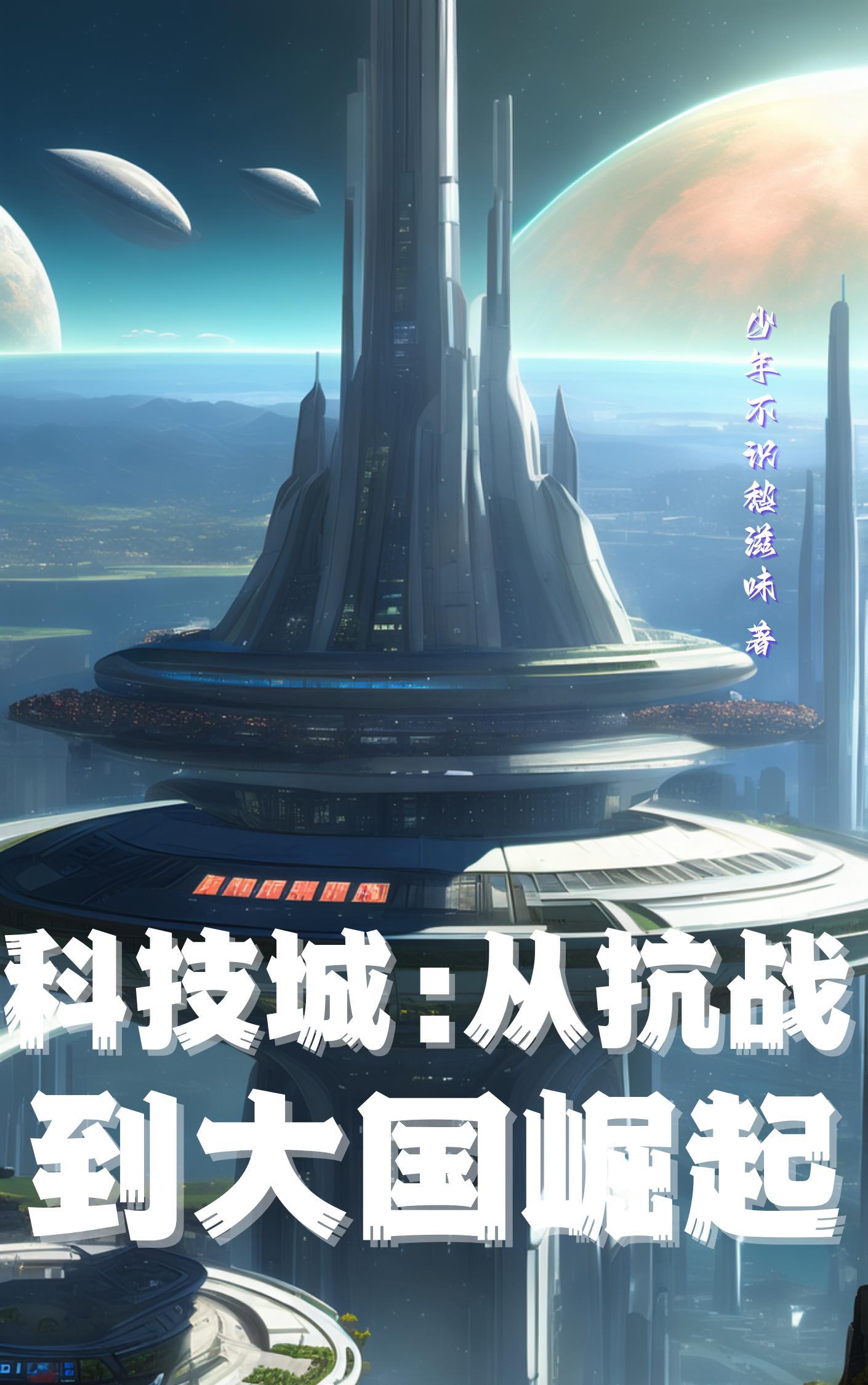凤阅居>非零和赛局 > 第63章(第2页)
第63章(第2页)
纪向薄无迹可寻的第三天,炼命师组织才得知他坐上了走私船,抵达日本,但东京血族至今风平浪静,说明纪向薄尚且潜伏着按兵不动。
长老团派出的三支小队出师未捷先折损了一队,考虑到纪向薄在血族的地盘,他们并不想大张旗鼓地增派人手,而是叫方蕲和白诗南,容时安三人和另一组人员先去东京,到达后切记低调,保守进攻,必要时候可请示长老团,
“你确定让那只实验体陪方蕲去?”施东岳表示怀疑,“那只实验体的底细我们都还摸清楚,你们就放心他留在组织内?”
葛老笑到:“施老呀,我问过小方子了,别人他都不要,只要白诗南。”
“哼……”施东岳不屑地说,“给阿猫阿狗取名字也算了,哪有给武器取名的,莫名其妙。”
“哈哈,年轻人的趣味。”另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聂长老自嘲,“我们老了,终将被时代淘汰喽。”
施东岳不悦,“没有我们这辈人打江山,哪来给他们享清福,就知道胡闹,添乱。”
“好啦好啦,你孙女不是也跟去了,你劝劝她,别总是和小方子唱反调。”葛老和颜悦色地说,“她弟弟的事啊,都过去六年了,该释怀了。”
施东岳脸色难看地说:“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小奕的事,我能体谅方蕲,小娜不行,你心疼方蕲,我也心疼我的儿孙。”
葛老叹口气,忧伤地摇头。
那件事,从一个满怀梦想的少年说起,再到虽死无悔的牺牲落幕。
方蕲的钱包里,翻开是一张十人的大合照,十个年轻人,笑容热烈且明朗。
“这个是我。”方蕲指着站在c位的自己,“当时还很青涩。
白诗南眼睛澄亮,“短头发的方蕲,也好看。”
方蕲捋了下小辫子,其实只有一梱长出的头发,被他用皮筋束起,算是对过去的缅怀和纪念。
“那时候我们队里,最小的才十八岁。”方蕲抿唇,鼻子酸涩,眼眶骤然红了,“十八岁,刚成年……”
白诗南抓住方蕲的手,捂到自己心口,心疼地问:“你很害怕死亡的离别吗?”
方蕲垂着眸。
白诗南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不会轻易死掉,实验体的生命不像人类那么脆弱。”
方蕲反握住白诗南的手,突然心血来潮地说:“小白,我们定个联手的法则吧。”
“法则?”白诗南似懂非懂。
“嗯。”方蕲眼里闪着光,“第一要活下来!第二,不是尽力,而是务必。第三,任何有智慧的生物都会判断失误,没有人不会犯错。第四……”
“没有第四条啦,就这三条吧。”方蕲想不出第四条,果断作罢。
白诗南欣喜,“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约定吗?”
“是。”方蕲笑靥坦率,“绝不能轻易挂掉的约定。”
死去的人死去了,活着的人在无尽的思念和痛苦中沉沦。
施安娜抱着满腔怨愤踏入东京的土地。
天气有些阴郁,空气中卷携着来自对流层的电气,冷风灌进领口,路边几个穿着超短jk裙的高中生跳着脚捂紧了围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