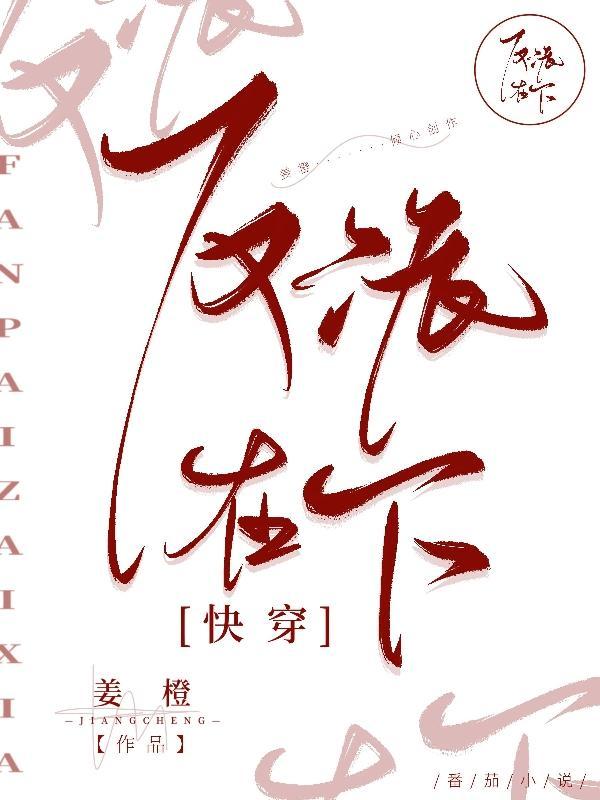凤阅居>沦落人的意思 > 第十七章 另隐玄机(第1页)
第十七章 另隐玄机(第1页)
贺广晟本想等三儿子惜载回来再召集一次家族会议。但长子惜厚似乎等不及。
他火急火燎来到贺广晟所居正堂,“爹,宜和行再不正常运营,这府上几百号人别说锦衣玉食,都要断粮饿肚子了。”
贺广晟双手负背,往侧边书房走去,“宜和行不是一直正常运行吗?”
惜厚跟着进了书房,“那叫还在运行,不是正常运行。你不在这一年多,我们都是靠此前已经有你签字、盖了左右掌印的单给入货出货。宜和行还压着几十万两银子只盖了左掌印的货单没有处理。城东仓房屯满了货,码头上黄埔口、神泉口、金沙湾口、双溪口、市桥口、虎门口、汕尾口等等,十几个口岸也堆码着宜和行的大批商货,干等着货单盖上右掌印才敢装船。洋人等急了也骂娘咯。幸好过去半年是秋冬两季,我只能以此为由跟洋鬼子推说等今年开春后,海关准许洋船入港就给他们装货。喏,这一入夏,洋人就开始催,于今已是八月,又快入秋了,十月底他们的船必须装上货离开广州,可是所有过五万的货单都只盖了左印,爹,这右印不盖,谁也不敢动那几十万的货咯,货不动,拿不出银子支付府上日常支出……”
宜和行的左右掌印由创立“五字号”商行的贺家太祖爷所刻设。那是一对取贺家太祖爷的左右母指指模、并在两边指模中央刻下“贺”与“五”——左贺右五,合成一对有效印章。洋鬼子叫它“商标”。洋鬼子之所以信任宜和行,喜欢和贺家做买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经历过百年考验的老“商标”。
在“五字号”改成“宜和行”前,商行规定所有入货出货单,金额过一万两白银的,必须盖有左右双印才能执行。一万以下则盖有左贺印章即可执行。在“五字号”改成“宜和行”后,资产和商品交易量翻了十几倍,故印章权限也有所长,这时规定金额过五万两白银都必须盖上左右两印章,五万以下则只需左贺印章。
左右掌印均由宜和行最高掌权人贺广晟掌管。平日里,贺广晟不公开地把左掌印交由他最信任的总管家六福掌管,方便行里办事,而右掌印始终由他自己锁着。
这次被捕后,他偷偷把锁右掌印的钥匙交给梁夫人代管,并交代六福,万一他在京城出事,由六福以左掌印掌管人身份与梁夫人一起召集贺府全体血缘亲系到祠堂选出宜和行继承人……
贺广晟静静倾听嫡长子长篇的唠唠叨叨,看着他急躁和抱怨。他知道正值壮年、精力旺盛的惜厚想得到右印掌权,得到右印就等于得到宜和行最高掌控权。贺广晟允许嫡长子有这野心,但他不止惜厚一个儿子,所以,在他没有完全看准时是不会轻易交印的。
等惜厚说完了,贺广晟仍坐在案桌前若有所思侧目看了他片刻,才微转头,在案桌旁的金丝楠木四方杌上的象牙骨烟架上齐整摆着的一排镶金、镶银、嵌玉、嵌宝石、木、骨或珐琅质的各式烟斗中,拿起最旧的、也是他最爱用的木制老烟斗,在案桌边沿轻轻敲了敲,抖出烟屑,又竖起吹了吹,不急不慢问:“你不知道宜和行并没有收到洋人的银子或花边钱或银票吗?”
“知道,可那是他们去年预订的货呀。”
老爷子依旧慢条斯理捣鼓他的烟斗,悠悠然道:“管他哪年预订的,没付银子急什么装货?”
“可,这些都是英吉利老商客,允许用老规矩——以货换货,有差价再用银子补齐,或立欠款账条,次年以货补差。”
“那——这批货是我们该给鬼佬补银子还是鬼佬该给我们补银子?”
“鬼佬有几样东西能拿得出手卖到中国?从来都是鬼佬稀罕我们的丝绸茶叶陶瓷等等各色上等好货,这次当然也是鬼佬得给我们补银子。”
“能补多少呢?”
“若出了全部囤货,可收货款大约四十七万辆白银,鬼佬带来的能互抵的洋货大约十万两白银,那么我们还能收三十七万两白银。”
“白银收到了吗?”
“目前只收到七万两,剩下的他们想立欠款条。明年再以货相抵。”
“收到七万就给他们装七万的货。其他的你替他们着什么急呢?反正盖印让他们装货、运走,你还是收不到现银,收不到现银还是没法支付府上各项支出,不是吗?”
贺惜厚哑然,他挠一下头,“这……”
贺广晟盯着他,“你有什么为难吗?”
惜厚脸色微变,忙摇头,“没。”
贺广晟狡黠敏锐的目光划过他的脸,又轻轻敲了敲烟斗,口气很随意,意思却意味深长,“这次鬼佬运来互抵的价值十万两白银的洋货是什么?”
“啊?”惜厚眼睛闪过一丝慌张,他抹一下额头,故作低头整理短褂衣扣,“还,还不是一些琉璃灯、钟表、会响音乐的盒子、更衣镜之类大清普通老百姓买不起、也用不上的玩意。”
贺广晟突目光威严,烟斗嘭声敲在案桌上,声音不高却郑重,“如果你敢黑里帮鬼佬走私那玩意,我要了你的命!”
贺惜厚吓得身子一震,扑通跪地,“爹,我哪敢呀。”
“不敢?!那我刚才随便一问,你紧张什么?”
“我,我只是想,若能和洋鬼子平等买卖倒也没什么不好,可惜咱中国人太实诚厚道,不肯丢国家颜面,不好的东西自己留着用也绝不准卖给洋鬼子,卖给洋鬼子的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出的特好的实实在在的头等商品,且都是些普通百姓用得上的生活品,价格又实在过于优惠,即使飘洋过海老远运去他们国家,他们无论贫富贵贱的老百姓也都还买得起用得上。只是鬼佬没啥适用的东西卖给大清普通老百姓,要是他们能运些价格低廉又是大清老百姓都实用的商品,那宜和行和鬼佬之间的贸易也就能扩大些。”
贺广晟何等老奸巨猾,随便拎个长篇回答就能搪塞他吗?他先是眼若饥鹰注视着没说真话的惜厚,沉思冷静片刻,突然鼻孔缓缓呼出一声叹息,目光一垂,缓声道:“我刚刚从这个鬼门关出来,你又想我进去吗?贸易扩不扩大朝廷自有决定,轮不到我们这些商贩的瞎出主意。我们老老实实做合乎大清法规的买卖即可。”
“是,爹,儿子宁愿自己死也不愿父亲再去受半点罪。这样的话只在这与爹说说而已,怎敢在外头贸然。”
“你这张嘴呀,但愿你别栽倒于自己这张嘴。”
“是,儿子铭记爹的教诲。”
贺广晟深叹一声,“去吧,你先去忙别的事。我梳理一下,是时候自会召齐兄弟叔侄等家人商议囤货处理问题。”
“是。”惜厚站起身,拍拍长衫膝盖处,转身要走,又挠挠头转身道,“爹,那个,易礼醇那孙女,好好一大家闺秀不在闺房学女红,母亲怎就让她跟着载官去上男子才上的私塾呢?”
贺广晟又给他一个严厉眼神,“易礼醇也是你叫的?按规矩你该叫他外祖父。易大人一时潦倒就连你也欺他?世事难料,他虽然年纪大了,流放边疆,他儿子吃不了苦病死途中,他却好好的活在边疆做实事。再说,他的孙女是学女红还是上私塾,是他爷爷交代过的。你关心人家一个小姑娘学什么做咩?”
惜厚感觉到父亲语气里的忌讳,其实按照父亲向来不苟言笑的脾气,今日已足够容忍他的放肆言行。惜厚不敢再多言,只是走出父亲书房仍一脸惋惜,心里嘀咕:一个温柔如水貌美如仙的女子,过个三两年长成了,嫁人做个“两耳不闻世间烦扰事、身心只享相公造的福”的小娘子不好吗?不知她爷爷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