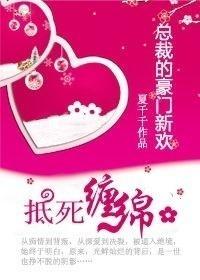凤阅居>雁南归歌词是什么意思 > 第7章(第2页)
第7章(第2页)
她脸上血色亦褪尽,“我”抬手,摸了摸右髻的发。
赵义巡眼过去。
她今日梳得是个双蟠髻,螺钿梳点翠其间,左右各簪了玻璃空瓶簪,簪头似瓶,可再插花。
现下左边的簪子还在,右边的明显被箭镞打烂,只剩下一截断尾。
赵义怒极,一转身发现邵梵已经单膝跪地,等在那里领罪。
几个大步,抬脚狠狠踢上邵梵请罪的脊背,一股脑地拳脚相加,邵梵不吭一声。
原来酒过三巡,气氛热络起来,听闻邵梵在军中夜视极佳,射术一流,每次都是夜袭敌营,屡试不爽。
赵义年轻气盛,平日也最擅弓骑,加之喝了酒性情上来,便当着赵洲的面,请求与邵梵于昏昼一比高下,赵洲欣然同意。
二人简装便策马复进林中,临时起意也未曾叫女眷回避,谁知赵令悦会碰巧也在林间?
邵梵到底是哪来的一百个胆子,能拿赵令悦的性命打赌?如若他马偏一步,又或是她躲一躲,那后果都不堪设想了!
思及此手不免更用了力,发泄了一通,对着赵令悦身边的人大声恼道,“带郡主出去!”
赵令悦被左右人扶着往林外走时,双腿还一直止不住地在发软,脑海控制不住的,开始回忆那日邵梵面见赵洲时的场景。
她也听到过赵洲与皇后议论,老修远侯死了,这次将他父子喊来,是要趁机收归军权的。
两相联系,赵令悦蓦然肯定了一件事——这个邵梵不是要害她,就是想要利用她。
她气地胸膛剧烈起伏,挣开雅翠岫玉的手,将那被他打断的琉璃发簪从发间拔出来,蓄力甩了出去,怒骂一声:“这个混蛋!”
雅翠和岫玉连忙凑上去给她顺气,“混蛋混蛋!白瞎长了双眼睛,敢叫我家郡主受惊?待禀报官家,看官家和大人怎么收拾他!”
赵琇得知赵令悦被偏箭打断发簪送回了家,立即与王献赶进了营帐,赵洲坐在上首,底下人都已经齐了。
邵梵脸上挂了彩,此时鼻青脸肿,赵义将林中经过禀报出来,言尾还愤愤讥讽,“儿臣倒不知这邵郎将如此看重输赢,一只鹿而已,跑了便跑了!竟还比得过昭月的安危性命去了!”
此话一出,宇文平敬即刻面如菜色。
他慌忙跪地求饶,“犬子怎会想要加害郡主?!定是喝多了酒糊涂了啊,看不清物也是有的,求官家饶这孽障一命!老臣半生无子,好容易得了这一个。”
又屁滚尿流地爬去了邵梵旁边,大力抽了邵梵两巴掌,“好在郡主无碍,官家郡主要怎么罚,只要饶他不死,都……都任凭处置!”
既赵令悦无事,赵洲也不能真的就因为这件事砍了邵梵。
反倒是宇文平敬这一番涕泪纵横,哭天喊地的,总归不好看,也扫了众官兴,“卿先起来,打也打了,骂也骂了,邵郎将,也是喝多了酒。”
邵梵伏地叩拜。
他有十足把握伤不到赵令悦毫毛,只言片语都不为自己辩解,直接伏到尘埃里去,“臣该死,是臣糊涂,眼盲眼瞎惊了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