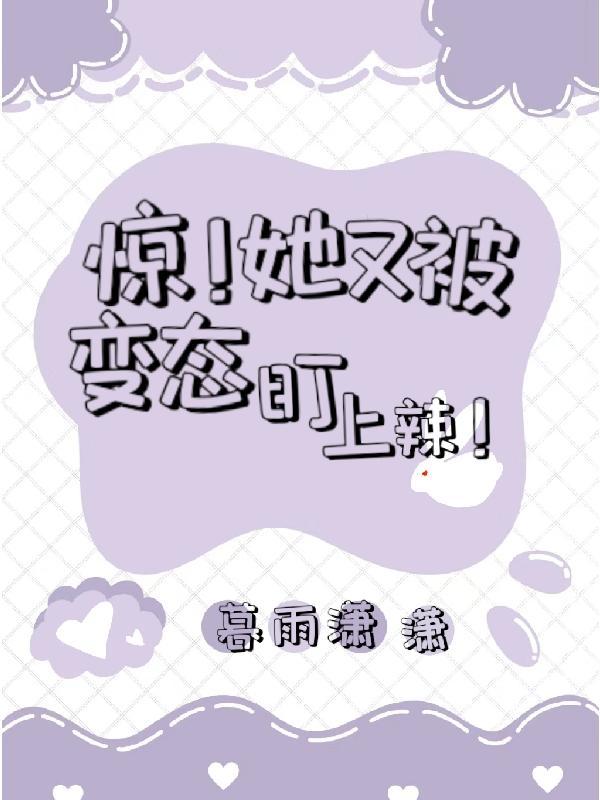凤阅居>送入敌国的将军lj > 第15章(第1页)
第15章(第1页)
钱副将会意,笑嘻嘻说:“郡王,您就先回罢,别忘了末将刚才说的话,云氏女——”
澹台怀瑾吊儿郎当地接话:“想得美,就算表哥不要,也是给我,你呀,排我后头去。”
钱副将一噎,悻悻道:“世子爷,您的后院已经人满为患了。”
“人多不多是一回事,按道理,是该先给我。”
两人争论之间,澹台桢已然站起来:“你们继续喝,我先回了。”
风信赶忙让出路:“郡王请。”
澹台桢脚步沉稳地下楼,近卫黎川一看澹台桢的脸色,暗道不妙,朝牵马过来的司南使眼色。
司南暗自叹气,还能如何,与黎川在两边护着呗。
澹台桢翻身上马,三人往州牧府去。澹台桢越骑越快,渐渐把两名亲卫甩在身后。门房听到外头有动静,忙忙开门:“郡王,您回来了。”
澹台桢一甩缰绳,大踏步进门,一路行至他暂住的留白居。里头灯影摇摇,影影倬倬映着两个人的身影。
底下静得很,一个伺候的人也无。澹台桢抿了抿唇,伸手推门。然而门从里面拴住了,推不动。
“谁在外头,我们姑娘要歇下了。”
澹台桢声如冷泉:“开门,我是澹台桢。”
里头静了一静,随后打开。澹台桢的眼睛越过惊疑不定的丫头,准确落在梳妆镜前的女子身上。
她才沐浴完,穿着藕荷色的寝衣,一头乌发披在肩上,发尾濡湿。眉如远山笼烟雨,目若杏花敛横波。身姿窈窕,气韵恬静。光是坐在那里,就像仕女画赏心悦目。
云意已从珍娘口中得知澹台桢的去处,觉得他今夜不会归来。于是便遣散下人,准备睡觉。未曾想到,会在这般情境之下,猝然相见。
进来的男子穿着大红喜服,身量极高,仿佛星夜旷野里一株笔直的树。他眉毛像是笔墨描过,粗细均匀。一双眼睛如寒潭古玉,又如古井暗泉,幽深不可查。高高的鼻梁之下,唇色如胭。
轩轩如朝霞举,朗朗若日月升。
澹台桢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径直朝云意走来,云意微微一笑,落落大方站起来,行礼如仪:“妾云氏,拜见郡王。”
螓首微垂,露出乌发之间白腻的一段细颈,鼻尖飘来淡淡香气,似雪似梅。澹台桢忽地想起钱副将的话:“郡王,你还记不记得,我胸口上的伤,就是云阔给砍的。等你享用完云氏女,赏给我罢,我非好好磨磋磨她,让她生不如死——”
望着新月初雪一般美丽清雅的女子,澹台桢忽地失语。她若是落在钱副将的手中,很快就会凄惨地凋零。
他,要不要她凋零呢?
太阳穴忽地一痛,眼前模糊起来,澹台桢勉力稳住身子,转身离开。
戒备的丛绿和行礼的云意都愣住:就这么走了,一句话都没有?
澹台桢行到庭院中央,忽然毫无征兆地,仰面倒了下去。
云意和丛绿吓了一大跳,跑出来扶起澹台桢。只见他双目紧闭,侧脸被地上树枝檫出几道细细血痕。唤了好几声,还是不醒。云意正想着要不要请大夫,两名侍卫打扮的人忽地出现:“打扰云姑娘了,我们郡王只是喝醉了,并无大碍,黎川和司南这就扶郡王去书房歇下。”
澹台桢一进来,云意就闻到了浓烈的酒气。可是澹台桢目光幽冷,两颊一丝红晕也无,云意还以为他并未喝醉。
“如此,你们快回罢,记得给郡王的脸上药。”
黎川和司南答应一声,架着澹台桢快速离去,心中懊悔不已。早知如此,他们就该拦着郡王不让他进去。若是郡王明日清醒,知道自己出了那么大的丑,非把他们俩抽筋拔骨不可!
叹,叹,悔之晚矣!
共同秘密
澹台桢一觉醒来,头疼欲裂。他坐起来,发现自己睡在书房里。榻边放着一碗醒酒汤,还是温热的。
看来,黎川与司南不久前才进来过。
揉揉太阳穴,昨晚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重现。他被澹台怀瑾一帮人披上大红喜袍,拉着去喝酒,大伙儿都闹腾,说今儿是他的喜日子,一杯一杯地灌他。他瞧着众人高兴,便从善如流。
后来,他骑马回到寝居,见到了云氏女,最后——
脸颊传来药膏清凉的气息,澹台桢腾地下床,高声唤:“司南!黎川!”
司南和黎川就站在门口,听到声音皆抖了抖,互看一眼,垂头丧气地推门进去:“郡王,您醒了。”
澹台桢面色沉如乌云:“昨夜我回留白居。你们怎么不拦着我?”
司南缩了缩脖子:“公主殿下曾书信来报,路途遥远,若是郡王想与云姑娘圆房,可便宜行事。属下们见郡王一回府就匆匆往留白居去,没好意思拦——”
黎川也道:“属下以为您要在留白居歇下,没想到您没说什么话就出来了。其实您就还差那么一小段路,就走出留白居了。”他边说边比划。
澹台桢扶额,事情已然发生,再多说无用。不知云氏女那边,是如何笑话他呢,若是传出去,他的脸面往哪里搁?
“云氏现下在何处?”
司南回答:“云姑娘一早就遣丫头来问候,还送来一碗醒酒汤。属下验过,没毒,就搁在榻边。”
过来问候还是过来笑话?澹台桢望向那碗尚温热的醒酒汤,鼻子轻哼一声:“唤云氏过来见我。”
“是,郡王。”司南极快去了。
澹台桢换上一身金青色绣菖蒲的锦袍,端坐书案前,好整以暇地等着。一刻钟之后,只听外头黎川道:“云姑娘,郡王就在里面,您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