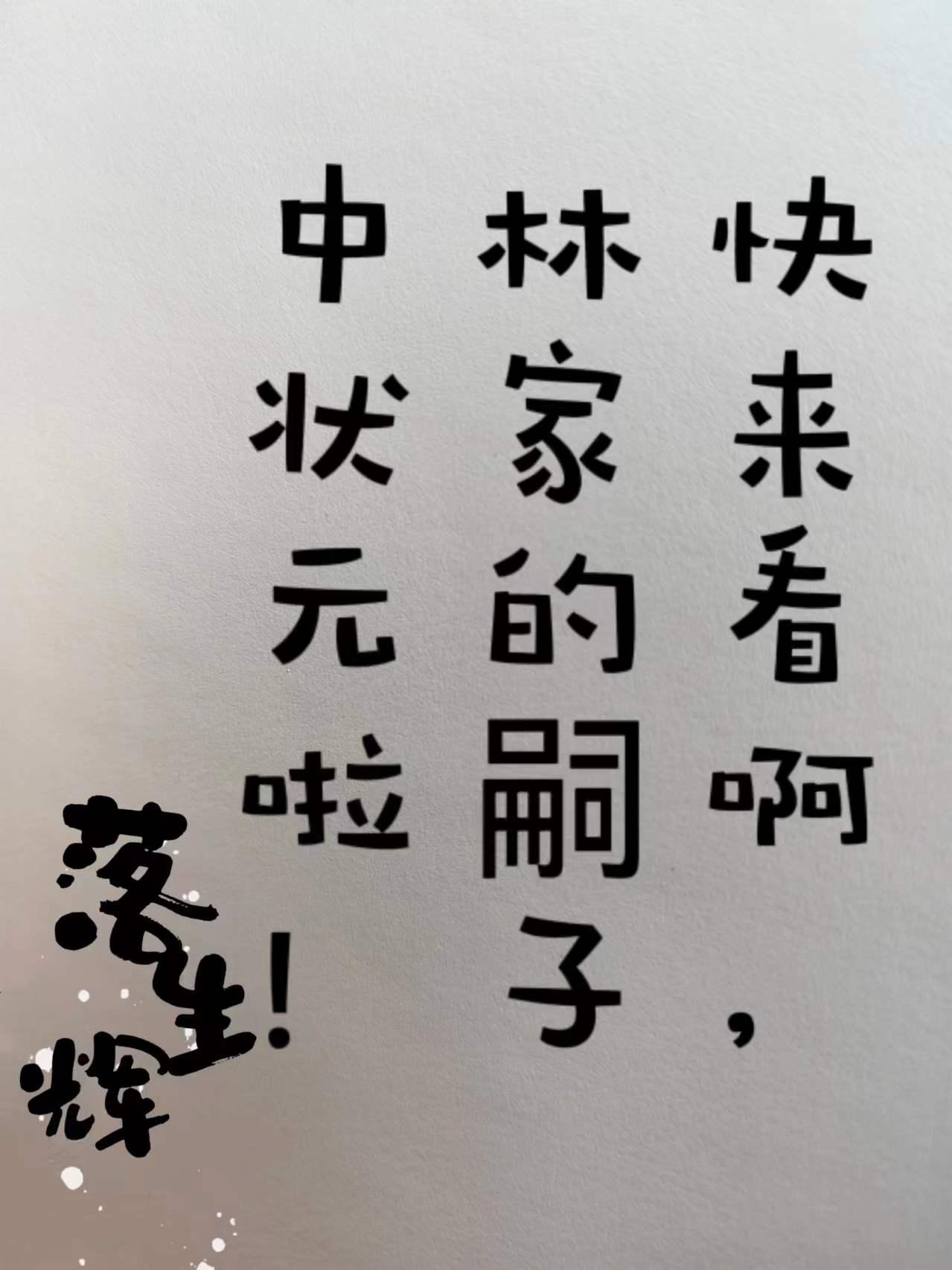凤阅居>娇缠 甜糯 > 第84章 展示体贴(第1页)
第84章 展示体贴(第1页)
“这几日下来,你们可有寻到,尚能一用的奴婢?”
抛开心里繁杂的思绪,苏玉昭心念一转,问起其他事来。
拾珠和银桃微顿,不经意相视一眼,拾珠道:“扫洒的丫鬟里,有位叫翠儿的,奴婢瞧她老实稳重,也不掐尖好强,最重要的是,她是家里遭了灾,被卖进府里来的。”
银桃撇嘴:“是老实,可就是太老实,打一棍子挪一下的。”
“这样的人,虽行事有些磨蹭,但胜在好掌控。”拾珠有不同的看法。
“那就再看看,咳咳,若是得用,再找机会提点她。”苏玉昭侧头低咳,眉眼有些恹恹。
此刻,她浑身都难受,脚腕上疼,肚子上疼,连骨头缝里,都隐隐的生疼。
银桃半坐在脚踏上,很轻易就现姑娘,疲惫萎靡的脸色,像是打不起精神来,心下略微一想,捡着一些好听的话,对姑娘说道:
“姑娘别忧心了,您被蛇咬的事,二老爷也知道了,还特意送来东西,叮嘱您安心养伤,依奴婢暗中猜测,二老爷肯定会替您做主的!”
“东西?”苏玉昭抬起眉眼,目光看向银桃。
“是二老爷亲自写的字。。。。。。”银桃爬起来,去到红木桌前,拿起一张卷起的宣纸,冲着姑娘慢慢展开,“姑娘您看,这字写得真好,等后面找时间,去把它裱起来,正好挂在正房里。”
“静,心,养,气。”苏玉昭一字一顿念道,脸上的表情蓦地寡淡。
“咦!写得是这几个字吗?”银桃弯腰伸头去看。
她素来不喜识字,尽管姑娘曾教过她,但因时日愈久,且自己也不上心,早就忘得差不多了。
拾珠脸色稍暗,一把将宣纸拿过来,迅地将其卷起,故作自然地说道:“这字虽好,却不适合姑娘,依奴婢来看,还是裱起来,挂到厢房去吧。”
长辈所赐,不敢随意搁置,但很明显,姑娘对这幅字,并不喜欢。
卷好的宣纸,重新回到桌面,拾珠端起棋盘,送到姑娘眼前,自然地转开话题。
“姑娘看看,这棋盘如何?咱们回来的急,您许多惯用的物件,都没来得及装上。。。。。。养伤的时日,又最是无聊,这棋盘来得正是时候,权当是给姑娘,消磨消磨时光。”
玉石的棋盘,上呈山水画面,四面包裹檀木基底,上雕虎龟兽纹,紫檀木的棋奁里,盛着黑白两子,白的莹润,黑的深邃,许是前主人时常把玩,黑白两色棋子,呈现温润晶莹的质感。
棋盘和棋子,皆是玉石,棋盘雕工精湛,线条流畅,棋子圆润细腻,精美不凡,不出意外的话,定是出自名家之手,不论是收藏,还是用来送人,都十分拿得出手。
苏玉昭目光下落,银桃趁机说道:“姑娘您看,这白子瞧着,像不像是蛋清?这一副玉石棋盘,一看就价值不菲,真没看出来,大姑娘不止生得好看,出手也这般慷慨。”
苏玉昭眸中兴味,不知不觉消散,淡声问道:“这是她送来的?”
银桃点点头,回道:“大姑娘,四姑娘,以及许公子,都有送来东西,分别有蝴蝶金簪,整套的青玉盏,黑白玉棋盘,以及两本诗集。”
“送东西的奴婢,是绮春园里的,蝴蝶金簪,在单独的锦盒里,黑白玉的棋盘,也是用匣子装着的,上面放着两本诗集,剩下的青玉盏,又是单独放在一起。”
“这些东西,都是一道送来的,也是搁在一起的,不过绮春园的奴婢,有特意说她们姑娘,怕姑娘您无聊,专门挑来两本诗集,给您平日打时间。”
诗集在黑白玉棋盘上,那这棋盘不出意外,也是大姑娘送来的。
至于四姑娘,对她们姑娘记恨着呢,哪会送来这样精美的物件?
不需猜都能知晓,那枚最廉价的蝴蝶簪,必定是四姑娘送来的。
拾珠来到床沿,轻声说道:“另外还有宋姨娘,替三公子送来一株野参,不过林姨娘和四公子。。。。。。”她顿了顿,小心地看着姑娘脸色,“哪面并未遣人过来。”
真论起来,比起三公子来,四公子与姑娘,该是更亲近才是。
苏玉昭淡淡颔,面上看不出异样,指尖拨过一枚棋子,眸底凉意悄然氤氲,状似无意般说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这说的是谁,不言而喻。
银桃兴奋的表情一怔,转头瞄拾珠一眼,小心翼翼地说:
“都是一府姐妹,她们来看望您,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四姑娘得除外,四姑娘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苏玉昭缓缓摇头,没打算和银桃解释,毕竟毫无证据的猜测,并不会令人信服。
只是见自己奴婢,对苏玉仪颇为推崇,心里多少有点不舒坦,加上身上又隐隐作痛,当即失了再说话的心情,对两人道:“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个人静一静。”
拾珠察觉出来,姑娘脸上的疲惫,把还想再说的银桃,拽住推出房间。
偌大的厢房里,就剩下苏玉昭,显得宽敞而空洞。
她脑袋靠着床柱,出神地望着床帐,半响,自嘴角泄出一声,若有似无的冷笑。
真是打得好算盘,想拿她来成全她,体贴温柔的名声,把她踩在脚底下,也得看她答不答应!
思来想去,无缘无故的,苏玉仪突然送来,这般贵重的物品,无外乎是踩着她,来展示她的体贴,身为同族长姐,对隔房的堂妹,关心爱护,情深义重,谁听闻不得赞她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