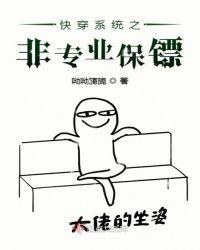凤阅居>归鸾全文免费阅读温瑜 > 第 46 章(第2页)
第 46 章(第2页)
他那般重的伤势,若是不上药,只用布带缠起来,伤口是会发炎的啊。
温瑜怔怔地看着萧厉满身的血迹,一股酸哑涌上喉头,她咬牙道:“骗子!”
他就是没有足够的药包扎伤口了!
怕她当心,还故意将伤口缠起来骗她!
当务之急是要给他退热治伤,温瑜强压下心口翻涌的涩意,拿起药壶,顾不得药是冷的,小心地把壶嘴放到他唇边,给他喂药。
奈何萧厉齿关闭得死紧,药汁全都从他嘴角溢出来了。
温瑜试了许多次都是如此,溢出了太多药汁,她不敢再浪费,望着半只脚已踏入鬼门关的人,眼眶发酸地抬臂
()抱住了他。
这逃亡路上的每一幕,都在她脑子里缓慢掠过,他背着她横翻山岭躲避追兵时额角滚落的汗,他为她挡下的那一道道伤,他被人摁在泥泞中打到吐血不止还望着她的一双眼……
一滴滚烫的泪就这么砸进了他领口。
她失去的已够多了。
温瑜目光在那无尽的悲意中渐凝,缓缓道:“我欠你好几条命了,我不会死,你也不许死。()”
她直起身来,拿起药壶自己含了一口,捧住青年的脸,苍白柔软的唇覆上他的,撬开他齿关,小心地给他渡了过去。
这次总算是没再溢出。
人命关天,这法子有效,她便也无暇再顾及旁的,如法炮制,继续给他喂药。
-
萧厉很久没做过梦了,大抵是这一宿的厮杀和压抑的情愫,唤醒了他一些久远的记忆。
他看到了软香罗帐和满室飘飞的红绸。
楼里的姑娘们总是将绸发拢在一侧,着轻罗纱衣半倚着门,眼波含情地目送恩客。
他单薄的身影跪在地上,冻得通红的手,拧起里冰水浸过的帕子,擦木质地板上人来人往留下的脚印,那无数扇或开或闭的房门里,传出无数咯咯的娇笑或似哭非哭的娇啼。
五六岁的他,尚不懂那是什么,但也知道不能听,不能看。
他尽可能地低着头,对那些声音,只有无尽的厌恶和恶心。
在楼道内巡视的打手听着那些声音,却会露出淫邪又龌龊的笑来,而每每同母亲相熟的男子寻来时,母亲和对方上了楼,那些打手们看着他,则会露出类似的神情,恶意又讥诮。
萧厉厌恶那楼上的一切。
他宁可去刷楼里的婆子们都不愿刷的恭桶,也不愿去楼上姑娘们房里擦地。
但那些打手总喜欢捉弄他,在萧蕙娘和他干娘们都顾不上他的时候,便会支使他上楼去做事。
擦地的抹布被黑靴踩住,看不清面目的打手将托盘塞到他手上,鄙夷又带着恶作剧即将得逞的兴奋朝他喝道:小杂种,把这酒送到霓裳房里去。㈤()”
萧厉垂着头,用力拽那截被踩住的帕子,声音冷漠又稚嫩:“我不去。”
身上便挨了一脚,狰狞的骂声钻入耳膜:“你不去让老子去么?得罪了客人,回头看老鸨不寻个人牙子把你给卖了!想靠着你那娼妇娘在楼里吃白饭,哪有那么好的事?”
他瘦小的身体被踹了个仰翻,害怕被卖掉,从此再也见不到母亲,忍着痛爬起来,端起递来的托盘,短了一截的袖子下,手臂上青紫的淤伤新旧交叠。
有的是被老鸨打的,有的是打手们捉弄他磕的,印象里,他在醉红楼就难有一身完好皮肉的时候。
叩响门,里边的声音支离破碎地让他进去。
萧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推开门,捧着托盘低着头走进,飘飞的红绸一直垂落至地。
他听见罗帐后的女人似十分痛苦地短促叫了一声,仓惶抬起头,看
()到的便是女人雪白的手臂被折按在锦绣被褥上,未完全合拢的罗帐里露出半张看不清面目的香汗淋漓的脸。
她身后面容更加模糊的男人恍若一条交。媾的野狗。
手上的托盘被打翻,他跟着哑叫了一声,捂住耳朵想逃离这地方。
后退中却像是一脚踏碎了无数面镜子,逼仄的房间跟着碎裂开来,变成了偌大的宫殿,他亦在这顷刻间从稚童变成了青年,床榻上的女人模样也逐渐清晰。
艳若芙蕖的一张脸,偏生了双清月般冷淡清透的眸子,被折按着手臂倒伏在床榻上,青丝铺了满枕,微红着眼望向他。
是温瑜。
萧厉浑身僵住。
那一瞬所有的惶恐和厌恶都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