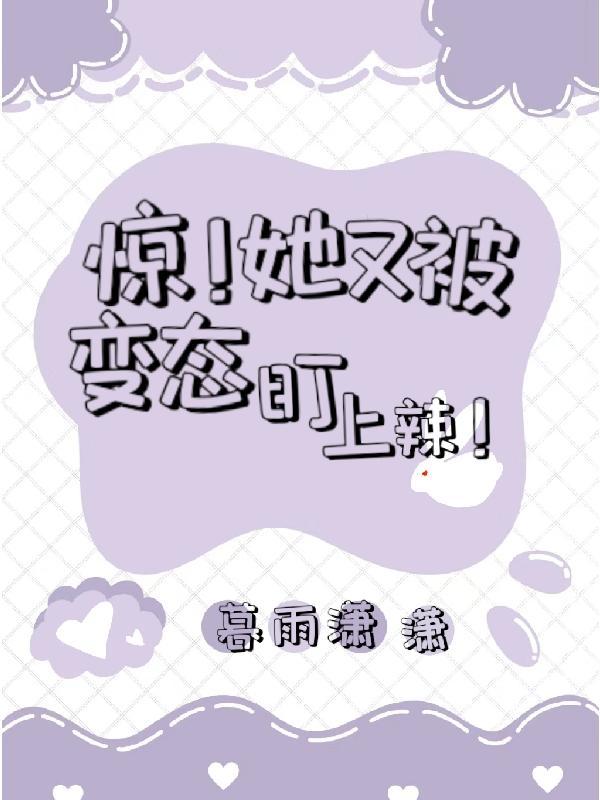凤阅居>岁事当长贺剧透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赵怀熠眉头皱了皱,声音放软了:“我不是那个意思,皇叔说什么都不算逾矩。可我的想法皇叔还不知道吗?我只是觉得委屈,连皇叔也不站在我这边。”
赵靖珩低声道:“事关国本,为社稷计,非寻常事,陛下不可任性。”
“皇后不是在陵寝里躺着?兰棠贤淑柔顺,恪守本分,我早已说过,能做皇后的女人只有她。”赵怀熠避开赵靖珩的视线,面色微冷。
提起那个名字,赵靖珩沉默下来。
翰林院学士孟玠之女,孟兰棠,亦是赵怀熠十六岁时迎娶的太子妃。出身书香官宦门第,才貌双全,性子柔和不失风骨,连太后都夸赞气度不俗。
或许是受先帝的影响,赵怀熠并不沉湎女色,迎娶太子妃后便确定将来的后宫之主非她莫属。
变故出在他登基前数月,太子妃忽然染上不知名的疾病,病症来得又猛又快,太医院尚未查出病因,短短十来日便急急病故,撒手人寰。
病得无端,死得蹊跷。
让从未动摇过的赵怀熠开始重新审视身边人,他当真是能掌控天下的天子吗?这些对他恭维臣服的人,是否又真的表里如一?
不尽然吧。
孟兰棠被追封为皇后,葬入皇陵。赵怀熠登基后再未提起立后之事,时不时被朝臣拿出来说道,不胜其烦。
“他们都盼着家族能出一位皇后。甚至,想让家族出第二位皇后。为此,不惜让你来说服我。”赵怀熠低下头,声音里带了些气性,“连我名义上最亲近的女人他们都要想方设法塞自己的人,我一个都不会让他们如愿。皇叔明知道,却一点都不体谅心疼我。”
赵靖珩注视他那从小便至尊至贵的侄儿,无声叹息。
太后的意图他当然再清楚不过,华家还有几个未出阁的女儿,她有意抬一把自家人。皇帝虽孝顺,在这件事上咬死了不松口,每次都用一句徐徐图之搪塞,太后找上他实在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
赵靖珩用柔和到自己都别扭的语气安慰:“好了,是臣的错,以后不会再提。”
“我可记着了。”赵怀熠抬起头,“况且,俞贵妃代为管理后宫,不也照样周到。有没有皇后,无伤大体。”
俞贵妃是工部尚书俞燔之女,恬静大方,宽厚仁善,颇有美名。若非皇帝执拗,赵靖珩觉得立她为后并无不可,刚才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只好作罢。
张全忠适时端上三份冰酪,赵怀熠殷切推到赵靖珩面前,让他尝尝。
无视那道视线,赵靖珩心不在焉舀了一勺乳白的冰酪往嘴里送,目光时不时落在第三只碗上——班贺到底什么时候能到?
鼻尖有点痒,班贺张了张嘴,那喷嚏到底没能打出来,抬手揉了揉,埋头继续往前走。
皇帝召见无非就是询问一件事,工事进度如何,越到期限将至越是召见频繁。有时遇上旬休日,宫里口谕传来,他也得认命立刻换上官服进宫。
身后内侍手中端着木匣,里边是今日他从军器局带来的几把鸟嘴铳,交由皇帝验视。
领路的内侍走了一条不常走的路,班贺满心满眼都想着一会儿如何应对皇帝,等回过神,一抬眼,已经到了校场外。
无遮无挡的烈日之下站着两个人,额上脸上晒出一层汗,正顺着脸颊往下淌。
班贺不由自主脚步缓了缓:“印俭,阿格津?”
险些晒迷糊的印俭循声看来,面露欣喜:“班大人,您怎么才来?”
“你们早到了?”班贺不自信地问,“那,殿下……也在?”
印俭希望他自信点:“殿下不进宫,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班贺看着四周,明明有廊亭:“你们怎么站在这儿晒太阳?”
阿格津终于第一次在班贺面前开口,用口音很重的官话控诉:“我不资道,那个人把我们领到泽丽,就邹了!”
但他已经找不到把他们领来的内侍了,两只手竖起食指一通乱指,漂亮的灰蓝色眸子充满困惑与委屈。
印俭安抚地把他双手按下来,表情是一种习以为常般的认命,带着破罐子破摔的洒脱:“我就说不要带阿格津,主子不听,这下好了。被连累的我才最冤枉,我就该在主子不听的时候跑肚拉稀躲进茅厕里。”
虽然不明白印俭为什么会这么说,但听起来很严重的样子。班贺对他们报以同情,打起十二分精神,走向校场内。
希望不会沦落到在太阳底下罚站,他怕热得很,这日头可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