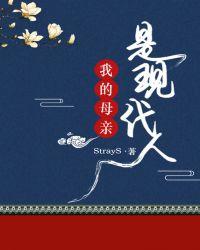凤阅居>长夏具体时间 > 第33章(第1页)
第33章(第1页)
郝总的一对一课程绝对是高强度,教完一遍马上就让龚希羽在他眼皮子底下独立练习。讲完基础又喜欢发散,还喜欢随时考问任何刚刚提到的其他问题。
龚希羽沉入忘我的模仿学习后,在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时间,就被郝总宣布时间到了下课。
还好,这个老师不会拖堂。至少会考虑到女学生的晚间夜路安全问题,所以还是到点就让她回家了。
学了一个晚上,龚希羽回到宿舍后,就没有再打开电脑,直接洗澡,躺在床上。她现在已经对于最后需要展示的东西保佑平常心,相信明天自己一定能够顺利将今天学习的东西反馈出来。
接着她开始打开淘宝,开始看起来自己需要改变的形象。她先搜了几套鲍言言的衣服,接着将同样品牌的其他同气质款式用图片搜索,最后价格从高到低,开始选最便宜的。
等到付款完毕,看着预计到货的时间,龚希羽开始盘算,她不会在白天实习的时候改变自己的风格。没有必要引起鲍言言或者其他同事的注意。可况万一她跟鲍言言撞衫,正品遇上仿品,比不过还尴尬。她决定之后先回这里换衣服,便装游戏只针对郝总展开。
龚希羽在经过了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一天后,最后不甚清晰的时候,总算能抽出一点点模糊时间来复盘一下自己对于将要勾引对象的进度。
她在这逼仄的单人床上,这个一看就是简约的床旁边正靠着窗户。其实晚间即使是这个时间外面总觉得那深蓝的天,亮的月光其实就些吵人。可龚希羽却不愿去拉上窗帘,有时候眼睛要用很大的压力去闭上,情愿将头和眼睛埋进被子里。
龚希羽很爱这里的窗外,可以看到远处的高楼和近处的茂盛的树。她清楚自己的心理,因为结束这个兼职后,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有机会睡在这样的房子里。却也不愿意真的那么清晰地对自己搞清楚这个想法。
龚希羽有时候会在已经哈欠和快要搭上的眼皮中依然机械地刷着手机,不愿意停止。有时候又越来越精神,索性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呆。
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即使自己白天的那些可笑可能也不自量力的计划,在晚上这样静谧的房间里再回想,不然不能清醒。
直到现在,其实龚希羽仍然不知道自己将会要怎么去“亵渎”郝总。她,可能是每天见过晚上的没有掺杂任何私人感情的只交流工作的郝杨,他在她的心目中当然是无法忽视客观那些男性标志,可更多的是他的冷静和耐心,打破了隔阂的那种平静而又能放松的他的气质。
可另一方面,白天的鲍言言又总是能轻易挑起自己的情绪,多种多样不愉快的难以发泄。她有时候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撇开这些冲突和针对,其实她自己也不自觉地被鲍言言的那些外在的女性标志所潜移默化。
郝总当然很好很好。如果他从头到尾只是一个遥远的顾客,可能自己不会有那么大的犹豫和不确定。可是他真的很好很好,不仅仅是鲍言言,配不上他。(当然是客观上的)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配不上。
自己是不是也陷入了那种对于富人的宽容?郝总对自己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又不是送了自己钱,只是这样的出于教养的友好和帮助,如果是一个一般人呢?即使是她也觉得条件很好跟自己不是一个世界的申恺,如果带入郝总做的这些事情,自己要去勾引他,会这样犹豫吗?
所以自己是不是也依然有一丝鲍言言的气质。
龚希羽不知道。
最后,在快要入睡的前最后一秒钟,龚希羽告诉自己,她没有做错,可能顶多从道德层面不光彩,可这座城市里面这些阴暗面还能少吗?在这座城市,多一个叫龚希羽的坏女人,只不过是海面上会产生的一滴水,压根掀不起任何水花。而她在做完了这些事情后,也不会在任何层面跟他们有什么交集。
好像忽然之间就降温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许在大洋彼岸或者是南极亦或非洲又生成了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大风大雨,一路千里迢迢,不断酝酿又壮大队伍,最终到达了沿海的城市这里。
好像只需要一瞬间,身体就忘记了之前的炎热,不需要任何时差调整和过度,就适应了目前降低了接近十度的温度。
龚希羽不太关注天气预报,或者说任何还未单独居住的女生也许在走出校门之前都会有这样即使看到了温度数字也不知道代表了什么服饰的含义。
可能龚希羽已经算幸运,因为这一天并不是这座城市里最难受的那种暑夏的雨天。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天气不让人烦恼。早晨拥挤的地铁里面可以给到多一个上班族挤进去的空间,却给不了多一把挂满雨珠子的阳伞。
于是在早晨匆匆的地铁站里,多了许多湿气,而这些水分没有给到润滑,反而增加了摩擦。被悄悄沾湿的手臂或者衣服,如果在冬天羽绒服的掩护下也许无法变成一场战争,可在夏季必然会引爆车厢。
地铁指挥员不知道在这个早晨目睹了多少这样的小型战场,不过当九点多,所有早高峰大站的上车站点开始逐渐降低人流后,刚刚还挤满了人的车厢就像米缸好像一下子倒空了一样。如果摄像头们有灵魂,它们一定会好奇这每天一幕幕小型的人流迁移。
龚希羽在每天穿过那个公司前方的大型十字路口的时候,看着一个一个的人面无表情地穿过马路,总会想起那种天空里的鸟群,一直忙忙碌碌一起拥挤地飞着,自发的又盲从的鸟类。没有任何目的地,也许终其一生就是为了一些虫子和吃食。不知道它们是否会理解天空、树叶或者是电线杆。是否会理解翅膀、羽毛和生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