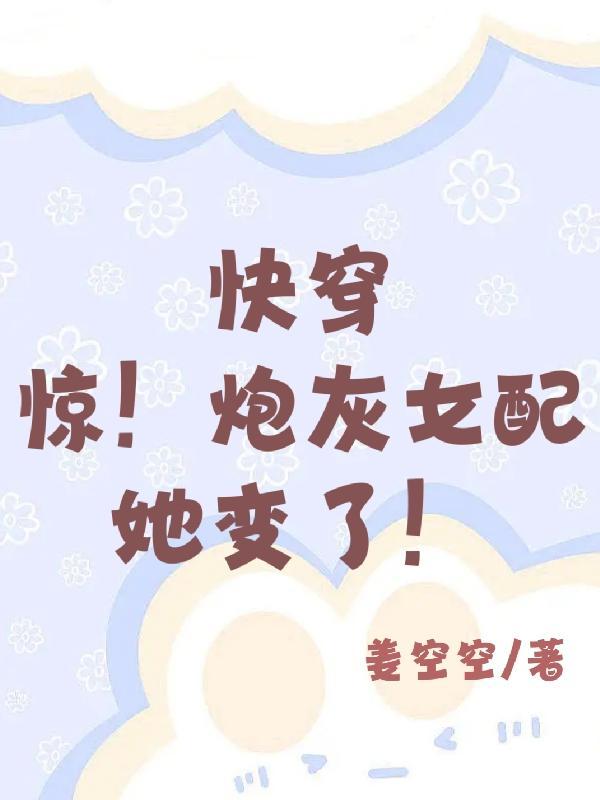凤阅居>嫁给暗恋的死对头免费阅读完整版 > 第63节(第2页)
第63节(第2页)
谢翎把虎鹤园的旧书房搬到了听荷院里,免去来回奔波,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书房被崔荷重新置办过,窗外四壁,藤萝缠绕,入门是一幅绣着山水壁画的屏风隔断,拐角处罗列松桧盆景,竹帘帷幕都用文雅的竹青色。
书斋中设了一张红檀木束腰画桌,桌上文房四宝齐全,旁边博古书架藏书堆叠,官帽椅坐累了,屋内还有榻几休息。
近来崔荷新得了一匹鸦青色的藤纹蜀绣锦,心血来潮要裁两件秋衣,隔三差五拿着软尺去找谢翎度量身形,过了四五天,终于做好了一件箭袖长袍,兴冲冲的拿来给谢翎试一试。
谢翎从榻上起身,张开手臂让崔荷为他换上,新衣的袖口处略有些长了,需要再收束几寸,崔荷唤银杏去拿来筐篓,坐在榻上掌灯给他修补。
谢翎把烛台往她这边挪了挪,说:“白日修补也不迟,夜里小心伤了眼睛。”
崔荷摇头,手中穿针引线,不带一丝迟疑,“就差袖口了,明天要去禅光寺,怕是来不及。”
她用这匹蜀锦给谢翎和自己各裁了一件,打算明天穿着一起去禅光寺参禅,她的那件已经做好了,就差谢翎这一套。
谢翎拗不过她,也就随她去了。
崔荷一边缝补一边问道:“我让你找的几个武官,都打听清楚身家背景了吗?可别背着什么感情债。”
谢翎搁下书卷,瞥她一眼,无奈道:“别急,等樊素把婚事取消了再说,你就没想过万一樊素不愿意取消婚事,你白费一番功夫?”
崔荷放下针线,疑惑道:“为何不愿取消?”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这不是樊素一人能够决定的,还得看她祖父的意思。”
“那我也得跟她兜个底。”崔荷也知道婚姻大事,樊素没办法自己做主,只是不甘心让她被蒙骗在鼓里。
樊素如今待嫁闺中,忙着给自己绣嫁衣,鲜少外出。
而她要忙着中元节祭拜事宜,也没闲工夫出门,恰好中元节要进禅光寺祈福,她就顺便邀约樊素一道前往,只待找着合适的机会告诉樊素。
二人各自坐在榻上,崔荷掌灯缝补,谢翎倚榻看书。
灯芯噼啪响了两声,谢翎担心烛火太暗,正要为她拨一拨灯芯,突然崔荷倒吸了口气,猛地抽回手指,像是被针扎到了。
谢翎起身来到她身侧,握住她的手指仔细看了一眼,葱白指尖上冒出了殷红的血珠,红得刺眼,谢翎毫不迟疑低头含住她的指头,粗粝的舌尖划过伤口,将血珠舔舐干净。
十指连心,崔荷的心尖也仿佛被舔舐过了一般。
柔软的触感带来阵阵颤栗,崔荷不禁想到漆黑夜里在她身上游走的暖意。
谢翎的舔舐不带任何一丝欲念,只想为她止住血,却在对上崔荷艳若桃李的脸颊时,与她产生了一样的想法。
四目相对,有暗流涌动。
谢翎心口一热,低头去寻她润泽的唇瓣。
崔荷嘤咛一声,撑住他忽然靠近的胸膛,呼吸乱了分寸,被迫压着仰高了脑袋,后颈被他死死扣住。
睁开眼,便见近在咫尺的谢翎眼中尽是掠夺贪婪之意。
他的吻强势而又凶狠,但托着她后颈时,又放软了力道。
松开时,崔荷身体已经软在他怀里,潋滟水眸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
谢翎低低喘着气,抵着她的额头,哑声问道:“回房?”
崔荷知道一旦回房,这一夜就没有了。
她手里的衣服还没缝好,明天一大早就得启程出发,不能耽搁,于是她摇了摇头,重新拿起衣服,手指还带着些颤抖,拒绝道:“不行,得把衣服修补好了。”
“明天再修也没事。”
“不行,今夜得弄好。”
说罢,她推开谢翎,重新执起针线要修补,谢翎见她如此执着,也不再多劝,只是盯了她须臾,见她又被扎到,这才夺过崔荷手里的衣服,自己缝补起来。
一根绣花针在谢翎手里像是没了脾气,听话的穿梭在布匹之间,须臾功夫,一侧的袖口已经收束完成,他又翻过另一侧依葫芦画瓢。
崔荷惊讶的看着他,他不是刻意逞强,而是真的会缝补。
崔荷轻声问道:“你为什么会缝衣服?”
谢翎掀起眼皮瞥她一眼,懒懒一笑,随意说道:“因为没有人给我缝衣服啊,小时候被人扯坏了衣服,不敢告诉母亲就自己缝补,去了军营,衣服隔三差五就破了,不自己缝补,上哪儿再买一件。”
谢翎垂着眼,平静的穿针引线,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摇曳的烛火映在他的脸上,将他的眼窝打出一道暗影。
看着谢翎孤冷的眉眼,她仿佛看到倔强要强的小谢翎挺直腰背,在众人唾弃谩骂声中摔倒又站起,又似是看到一个少年将军在黄沙漫天的西北塞外踽踽独行,身后是旌旗烈烈,尸山骸骨,断刃划过黄沙,留下一条蜿蜒的痕迹。
崔荷轻轻靠到谢翎的肩膀上,柔声说道:“以后有我给你补衣服。”
谢翎手上动作停顿片刻,心中蔓延起一股暖意,眼底流露出柔情,淡淡笑了笑,没有回话。
摸针时分了神,指尖传来一阵刺痛,他低头一看,被扎到了,把手递到崔荷面前,皱着眉故作委屈道:“夫人,我受伤了。”
崔荷低头一看,确实出血了,她从怀里掏出手帕要给他擦拭,谢翎却拒绝了,抬起手来不让崔荷碰到。崔荷扭头看他,见他目光灼灼,哪儿有什么委屈。
谢翎低哑着嗓子引诱道:“礼尚往来。”
崔荷脸上一阵发烫,耳尖都泛着红,她怎么做得出那么孟浪的行为?当即摇头拒绝。
谢翎失望的说道:“原来夫人只是嘴上说说,其实完全不在乎我的死活。”
崔荷觉得好笑,嗔怨的看着他:“扎了一下叫什么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