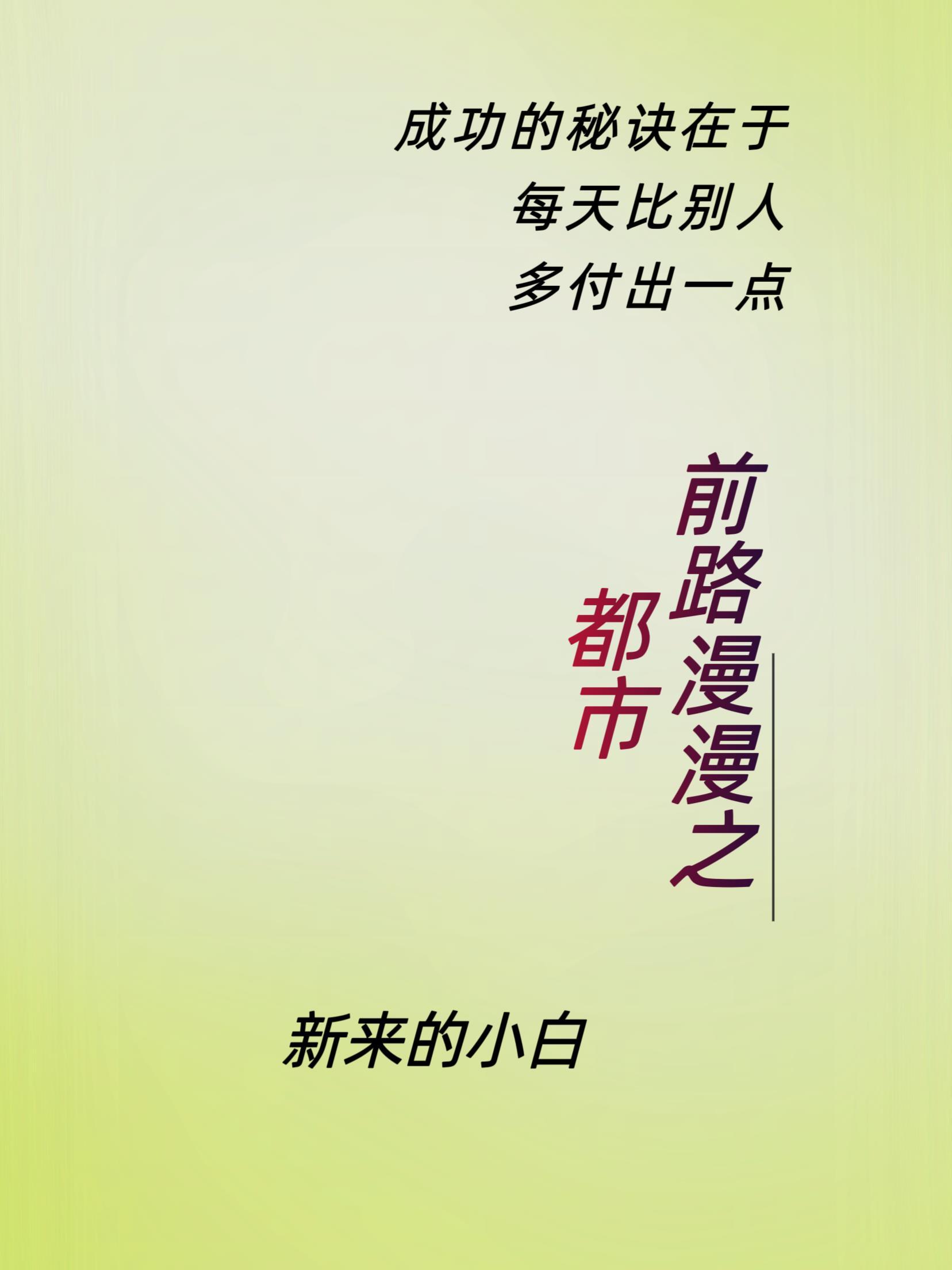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京洛再无佳人1全文免费阅读 > 第77页(第2页)
第77页(第2页)
车辆过了火器营桥,开上了北四环西路。
出了四环,机场就快到了,沈敏看了看表,比预计时间还早了约莫二十分钟,他略微松了口气。
后座赵平津的电话响了,他睁开眼看了一眼,没接。
然后停了一会儿,又响。
赵平津按掉了。
沈敏坐在司机旁边,不敢大意,悄悄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这时手机又开始响。
赵平津终于接了起来,嗓音听不出情绪:“喂?”
陆晓江的声音,混在电话那头嘈杂背景之中,遥遥地不太真切,却带着分明的紧张和局促:“喂?喂?舟舟?”
赵平津不耐烦地应了一句:“是我。”
陆晓江那头在播放机场的登机广播:“我在香港机场,我爸的赴美签证昨天到了,我昨晚给你电话,你没接。”
赵平津受不了那份嘈杂,微蹙着眉头,随口应了一句:“有事?”
陆晓江说:“我半小时之后登机。”
赵平津仰头靠在椅背上,抬手捏了捏眉头。
他漫不经心地望了眼窗外,已经是市郊,山坡高低起伏里有低矮的树丛,残雪挂在枝头,冬天里枝叶落了,灰蒙蒙的一片萧瑟不堪,今天风大,路旁卷起漫天的灰尘。
陆晓江在那头开始说话。
赵平津的脸色慢慢地变了,下一刻他忽然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你再说一遍。”
整台车子忽然陷入寂静,整整十多分钟,沈敏没听见他再说一句话。
沈敏回头看他,电话仍然在耳边,他整个人的神色却完全地变了,紧紧地抿着唇,牙根都咬紧了,脸上浮现一种几乎是僵硬而暴戾的神情,连着整个人,几乎都在微微颤抖。
沈敏心底惊慌一跳,立刻打手势示意司机稍微降慢车速。
就在那一刻,他忽然听到了赵平津的声音。
那声音,仿佛被人死死地扼住了喉咙,气息低微,濒临死亡。
他微弱地问了一句:“这么些年了,你就没想着告诉我?”
车里又陷入了一片死寂。
赵平津低低地喘了口气,声音却仍是微弱到得几不可闻:“你说的这些事儿,我也理解,只是晓江,咱俩的交情,到这就尽了。我不会再见你,你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如果你要跟我们共同的朋友见面,你请便,无论是在这北京城里头还是任何地方,我不会出现在任何有你的场合。”
陆晓江耳边紧紧地贴着电话,他打这通电话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是一个毁灭性的结果,他抖着嗓子带了一丝哭腔:“三哥……”
赵平津的情绪压抑到了极处,甚至带了一点诡异的温和:“晓江,黄西棠身上受的那颗枪子儿,原该是你的。”
陆晓江忽然觉得害怕,举目望了一眼机场的人声鼎沸,身上无法抑制地打了个寒战:“你今天结婚……”
赵平津笑了一下,那笑声急促仓皇,仿佛一声夜枭的啼哭:“你还知道我今天结婚?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接陕北来的那位。”
陆晓江心存了最后一丝幻想,迟疑了好一会儿,嗫嚅地道:“三哥……求你原谅我。”
赵平津淡淡地答了一句:“再见,晓江。”
赵平津仰起头,望见混沌沉重的天空,那一刻忽然想起小时候住在大院里头,夏天的午后,天是透明的蓝,他跟晓江儿、高积毅他们几个调皮捣蛋的男孩儿,正午趁着大人们都睡了,悄悄溜出来,瞒着大人们翻墙爬出去,在胡同的墙根下踢球。
那时的阳光真好啊。
沈敏直挺挺地坐在前头,大气都不敢出。
司机刘师傅跟沈敏交换了一个眼神,刘师傅跟了赵平津好几年,老刘见过他撒火,见过他摔东西,见过他把下属骂得面无人色,但从没见过他这样令人胆寒的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