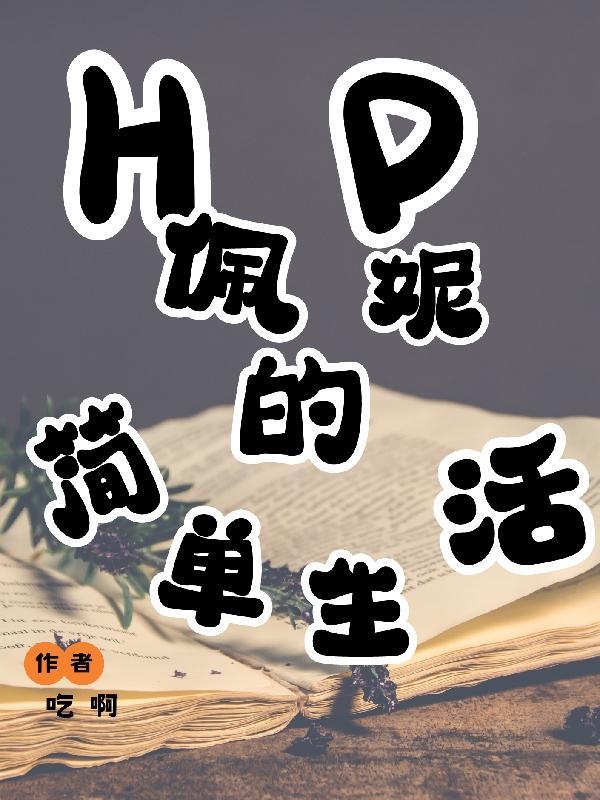凤阅居>葡萄酒恋爱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这时,陆和暄问:“那将来,我可以去岭南那边找你吗?欢迎吗?”
“当然欢迎,”司徒安然忽然伸手搂住陆和暄的后背,就像姐姐搂着弟弟那样,“我在深圳工作,我的家在离深圳不太远的小城市,很舒服,我时不时就回去。深圳这种大城市没什么好看的,到我家的祖屋看看吧,美着呢。”
“祖屋?”陆和暄对这个词非常感兴趣。
“是的,就是祖上传了几代的老屋,里面还供奉着列祖列宗,以及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
陆和暄很高大,虽然司徒安然搂着他的后背,但她的头也只够到他的肩膀。她的脸紧紧贴着他结实的肩膀,可以闻到他身上特有的男子气息。风吹过,她的长发一丝丝撩拨着陆和暄的脸。
她知道她的行为过于出格,但她只是一名女子,情感终究战胜了理智。而且她感知到,陆和暄也渴望这样。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就像认识了上百年,灵魂冲破了十年的年龄差,融合在一起。
“而且,那是一幢非常漂亮的碉楼,至今有一百年历史了。这是一代代的传承呀!”
陆和暄对这座他工作生活了大半年的他父兄的大酒庄,没有太多感觉,但是对司徒安然口中的碉楼祖屋,却忽然生出向往之情。那是然然姐的家啊。“说说那是怎样的,我没去过岭南。”
“我们那边的碉楼,很多都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前的祖先建的。他们大多从西洋、南洋归来,看到那些地方的房子是那样建的,于是买了原材料回来,再结合我们当地的建筑特色,建立起这些中西合璧的碉楼。
“我们家那栋碉楼,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回来建的。他去了西洋,赚了些钱,回来后就在村里建的。据说跟他一起同去西洋的人,都回来建起这样的碉楼。
“我无法想象刚建成时,在那个年代,这些碉楼是多么震惊的存在。因为即使放在百年后的今天,当你看到那些雕梁画栋、飞檐翘角,你还是会被细节处的美学所打动。那是整合了东西方美学精粹的、独一无二的。
“我自幼在这栋碉楼长大,初中才到城里。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家碉楼有多了不起,后来到城里上中学,到广州读大学,到深圳工作,再全中国、满世界地走,才意识到,我家那栋碉楼,是多么的伟大。
“后来,我在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乡间,看到一些高高的碉楼。它们的建筑风格与我家那栋碉楼挺像。应该是,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人也来到美国,在那里建立起这种风格的碉楼,我那位老祖宗下西洋时看到,就把它学了回来。
“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很远的地方,也渐渐意识到,远方即使再好,也是远方,走遍天涯,我都在渴望回家。”司徒安然的低声耳语,似乎有无穷魅力,陆和暄都听得魔怔了。
“然然姐,我很羡慕你,因为你有家可归。”良久,陆和暄低声说。这是他的真心话,他与那个人,都在羡慕这位来自遥远南方的女子。那个人羡慕她自由且独立的灵魂,而他羡慕她有家可归。
“每个人都有根,”司徒安然小心翼翼地说,生怕触及到暄儿的伤,她曾听闻他没有家,“就像这些绿植,”说着,司徒安然另一只手轻轻拨弄着那些矮小的碱蓬,“即使生存环境再恶劣,但因为有根,它们生生不息。”
陆和暄苦笑一声,说:“我就没有根。”
司徒安然的心像被人揪住似的,有点疼。“可以讲讲你的故事吗?我们认识这么久了,你都没讲过你的事。为什么不在学校呢?”
有那么一瞬间,在司徒安然那温柔甜美、像有魔力的声音中,陆和暄想把他所有的烦恼与苦楚,全都倒出来。他需要一个聆听者,他太凄惶、太无助,他还是个孩子。
但稍微冷静下来,理智告诉他,不能让然然姐看出他的脆弱。一个只知道诉苦的男人,是不可能与然然姐站在一起的,不配。
他渴望进步,渴望取得一些成就,渴望变得出色以配得上身边这名温柔待她的女子。但是,路在哪?他眼里是有光,心中是有梦,然而,脚下并没有路。
思量片刻,他幽幽地说,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没有父亲,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不在了,是外婆养大我的。外婆今年初也走了,她没有别的儿女,因此我也没有表兄弟表姐妹。”
淡淡一句话,讲述了几个人的一生。
虽然早就听说暄儿无家人,但真从他口中听到,司徒安然又一阵心痛。她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28年来一直顺风顺水,只除了近段时间被李凌云劈腿。她觉得她的世界坍塌了,殊不知已比暄儿的好太多。
暄儿,从他没有父亲那天起,他的世界就已经坍塌了。
“那为什么来西北呢?在山东老家不好吗?起码是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即使没有亲人了,也还有朋友,还有街坊邻里。”
而他却不能告诉她,自从他从外婆口中得知生父的信息,他就渴望来到生父的地方看看。看看那个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看看那个父亲为母亲所建的酒庄——莲石酒庄,看看那个人——那个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虽然决定不相认,但是他们都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渴望与他们近点再近点,哪怕只是远远地、卑微地看着他们。或许,这就是然然姐说的“根”吧,即使他没有根,也对根充满渴望。
“不想念书了,不想再待在那个小地方了,就是想到外面走走看看。因为我是没有根的浮萍,所以可以去很远的地方而没有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