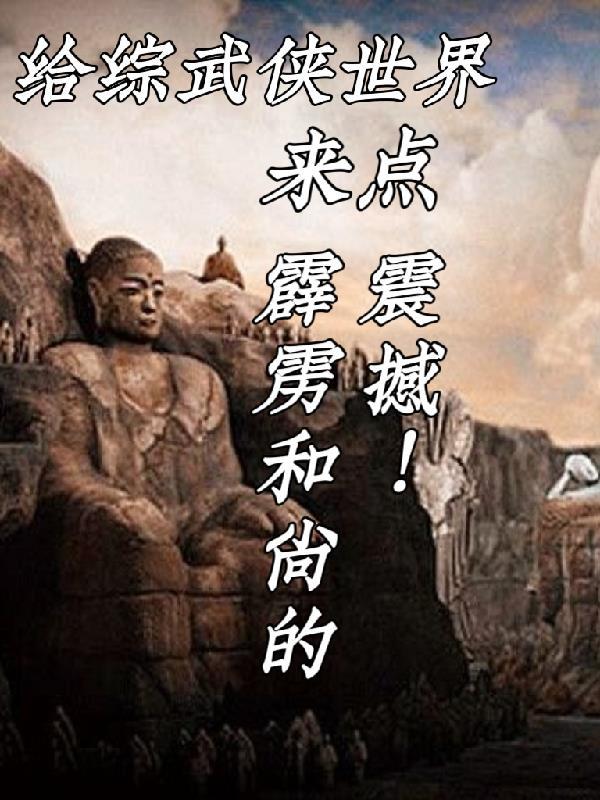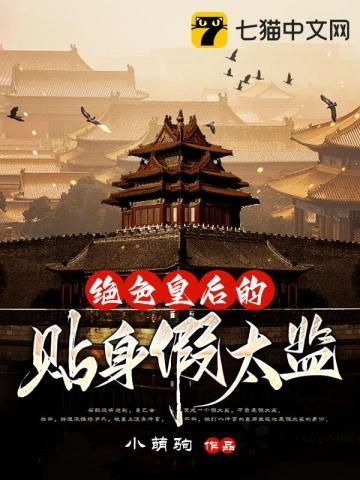凤阅居>失忆后她又凶又撩女主叫什么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谢凛呼吸微顿,快步道:“把季闻叫来。”
谢凛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进了内室看着塌上陷入昏迷的人。
她的一双眼睛紧闭着,脸色素净惨白,静静躺在那里,没了往日见到自己时张扬生动的神情。
一只纤细的手露在被子外面把脉,下午他笑她打扮得像个多宝阁的时候,她腕上戴的就是这样的镯子。
一旁的季大夫眯着眼睛把脉,过了会儿道:“呛了水,好在不多,没有伤到腑脏,方才的药煎了喂下去,把水吐出来。气滞血瘀,脉搏沉细,但年轻身体底子好,我开个扶正固本的方子慢慢养着。只是前额受了伤,这要等醒来再观察症状,看看有无影响。”
谢凛点点头,看了几眼,没在里间多呆,交代侍女砚秋带人好生照料着,便离开了。
过了一个多时辰,砚秋进了书房。
谢凛垂眸一边翻看着手中的书信,一边正听旁边的侍卫汇报。
待那人回完话行礼出了书房,砚秋上前说道:“世子,卫娘子好像要醒了。”她略顿了顿,好像有点不太敢开口:“在喊您的名字。”
“我?”谢凛薄薄的眼皮微跳,感到几分不可置信。
室内空气中浮动着浓烈的药味,床上的卫瑛依旧紧闭着双眸,气色看起来比刚捞上来时好了很多,唇瓣透着粉,一张玉白的脸陷在乌发里,额头上包着块纱布,整个人睡得并不踏实,秀气的眉毛紧锁着,好像魇住了。
砚秋拿帕子把她脸颊上渗出的一层薄汗擦了,道:“给娘子喂了药,吐了一些水出来,好在没发热,检查过身上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谢凛还没说话,卫瑛突然在昏迷中口齿含糊地喊了句:“谢凛……”
除了国公爷和长公主,素日里鲜少有人敢直呼世子的名字,一旁的砚秋吓得不敢言语。
谢凛微微怔住,莫非她对自己情根深种?那为何还把二人的婚事给拒了?
他细细回忆往日与她的每次偶遇,想她说过的话,试图从细枝末节处找到答案。
还没等他想明白,床上的卫瑛再次在睡梦中开口,斩断了他发散的思绪。
“狗贼。”
谢凛气笑了,这人晕过去了还不忘骂自己。
他在心里细数卫瑛骂过自己的话,现在又添上一个。
好在谢凛自认还算大度,不跟她计较。
离开前谢凛吩咐道:“让季闻再开个补身子的方子,告诉他用最苦的药,”他望了一眼床上仍在昏迷中的卫瑛:“等她醒了喂给她喝。”
天色未明,梁宅院内众人惊慌失措,女眷叫喊声此起彼伏。
谢凛在马上瞥了一眼,并没有为难梁家的女眷和下人们,只命人拿了梁同裕。
“谢大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雨刚停没多久,地面积了很多水,拖行间梁同裕的衣服被污水弄脏,失了体面。
“是不是误会,梁大人自己清楚。”一旁的侍卫举着火把,火光照在谢凛的脸上,照得他骨相凌厉流畅,眸中藏锋,眼神冷冽。
梁同裕深吸一口气,努力想挺直腰板,昂起头道:“下官行事,皆奉齐王殿下之令,谢大人凭什么拿我。”
说话间梁同裕的见自己的儿子也被擒了,脸色铁青,语速变得急促:“齐王和太子斗法,你谢家何必掺和进来?”
旁边梁同裕的儿子梁亥被捆了挣扎不开,骂道:“你要造反!”
闻言,谢凛轻笑两声,他笑得无害,却让面前的梁家父子感到一丝寒意。
谢凛一手握紧缰绳,俯下身来,用剑柄抵住梁亥的脸,居高临下道:“我造的哪门子反。”
说完他失了耐心,对一旁的蒋海扬了扬下巴,调转马头离去。
蒋海心领神会,命人将梁家父子捆了捂着嘴带走了。
日正中天,谢凛在书房唤来侍卫重云:“你回一趟上京,查查卫家。”昨夜卫瑛被救起来的时候重云也在场。
重云应了,回完话前脚刚出书房,就碰见砚秋急匆匆赶来。
俩人打了个照面,砚秋没来得及说什么,略擦了擦一路赶来额角溢出的汗,进书房禀道:“世子,娘子醒了,只是……”她话语一滞,补充道:“只是她好像失忆了。”
卫瑛醒来盯着头顶的绣花床帐,眼神空落落的,她感觉自己睡了好久,醒来浑身都疲软酸痛。
最糟糕的是,她怎么都想不起先前遭遇了什么,甚至连自己姓甚名谁都忘记了。
思及此处,卫瑛气得想锤床,失去了记忆,那还不任人捏扁搓圆?
“是啊。”听到有人悠悠接话,卫瑛才发现自己下意识把心里想的说出口了。
她翻身望过去,先映入眼帘的是劲窄的腰身,来人穿了身墨绛红的圆领窄袖袍,手臂上缠绕的护腕衬得他的胳膊线条修长利落。
他的身量很高,她需要用力仰着脑袋才能看到他的脸。
是很漂亮的一张脸。睫毛长而直,眼眸深邃有神,鼻梁高挺,唇瓣浅红,此刻正敛着眸,居高临下地望着自己。
卫瑛细细打量他,惊艳之余还让她感到熟悉,应当是失忆前认识的人。
“你是谁?”她试探着开口,昏迷了一整夜,此刻她的嗓音略微沙哑。
旁边的侍女端来一盏温水慢慢喂给她喝,被水润过,卫瑛才感觉嗓子舒服多了。
“我是……”
你最讨厌的人,被你拒过婚的人,你睡着了都要骂的人……谢凛思索着怎么说能让她更诧异。
他扯了把椅子在雕花拔步床边坐下,劲瘦的长腿随意支着,姿势散漫道:“你的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