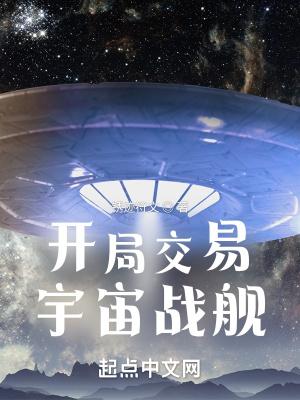凤阅居>妹妹皇后免费阅读 > 第63章 你以为崔家的胆子就这么点吗(第2页)
第63章 你以为崔家的胆子就这么点吗(第2页)
危玠一字一顿的吐露:“是武器。”
在边境走私武器,崔家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简直呼之欲出!
“你以为,他崔珩是为了你,才一时兴起要反抗我?那他这些年来的筹谋,是个笑话吗?”
凌玉毛骨悚然,颤着声:“皇兄……是如何得知的?”
他以冰凉的指腹轻轻摩挲女郎白玉似的下巴:“今日,小玉不是亲眼所见了吗?天高皇帝远,这凉州活阎王的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凌玉眸光一动,忽然握住了危玠的手,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迫切的握住这个男人的手。
“皇兄,该怎么做,才能真正帮助她们?”
凌玉眼中早已蓄积泪水,同为女子,她愤恨那些人的恶行,可又深感无能为力,泪珠悄然滚落,砸在男人的衣袖上头。
这一路上,她见到了许多在深宫中从不曾见过的场景,托儿带女,被丈夫毒打而赶出街头的可怜女子,瘦的皮包骨头,无可奈何卖孙子孙女的老汉,还有路旁奄奄一息的少年……
太多太多了,可与这些人间惨烈相隔的另一条街,是世家门阀穷奢极欲的销金窟,红烛昏罗帐,金迷纸醉。
崔家走私武器盐铁,中饱私囊,日复一日越肥润,却还要虚伪的要个人人夸赞清风劲节的名头,真是可笑……
大周中流砥柱、帝王肱骨之臣、清流世家,不过是掩盖他们欲壑难填之欲望的遮羞布罢了!
受苦受难的永远都是百姓。
若是阿耶还在就好了。
她就还是那个被娇惯的公主,遇世事不平,不忿子民的苦难,全都可以告诉阿耶,阿耶会坚定不移站在百姓身后,站在自己身后,那么,她就可以解救于苦难中挣扎的百姓,严惩崔家!
可惜,这一切一切的,在自身弱小的面前,都变做了痴人说梦。
她如今,哪里还有资格行使公主的权力呢?门阀势力尾掉不大,她贸然行事,怕是更会连累那些可怜的人儿,到头来也折了自己。
崔珩逃了,可他背后的势力还在……他是崔家最年轻的家主,这一切罪恶,都在他的默许之下生,原来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他啊。
记忆中,那一袭温柔又总是令自己感到依靠的雪袍,渐渐模糊,凌玉觉得胸膛处上涌了一股腥甜,可她硬生生忍住了。
危玠静静地凝着面前的女郎,他清晰的感受到,她的手在不停的颤抖,有愤怒,有怜悯,更多的是被欺骗后的绝望。
凌玉不敢开口,她知道,强悍如皇兄,或许也无法做到,在门阀势力下独善其身。
危玠叹息一声:“事物皆存正反两面,正是因为崔家这颗毒瘤,才导致西域十部多年战乱,分裂至今,便不会对大周造成太大的威胁。”
“哥哥有时候也想学一学崔珩,满口仁义道德,故作高洁君子姿态,或许小玉就会多看我一眼。”
“可惜,哥哥永远无法清风亮节,有些营营苟苟的事,总得有人去做,不择手段的维持大周运转,是登基那日,对天道许下的承诺。”
危玠不太夹杂感情的世界中,从来只在乎目的是否达成。
眼睁睁的看着子民们于水生火热中挣扎求生,凌玉忽然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滚落,大滴大滴怎么都流不尽,笑的那样苦涩,那样无可奈何。
危玠却于女郎的面颊上,窥见了她生平第一次……如此绝望的伤心。
自回京后,凌玉在他面前哭泣的次数,数也数不清,恐惧的、厌恶的、憎恨的、委屈的……他全都见过,可从未见过,当下这番,平静下浓烈的绝望感。
女郎的声音很轻很轻。
“危玠,我们走吧。”
她平静的直呼他的名字,热泪滚烫间,转过身,不再看那悲惨的一幕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