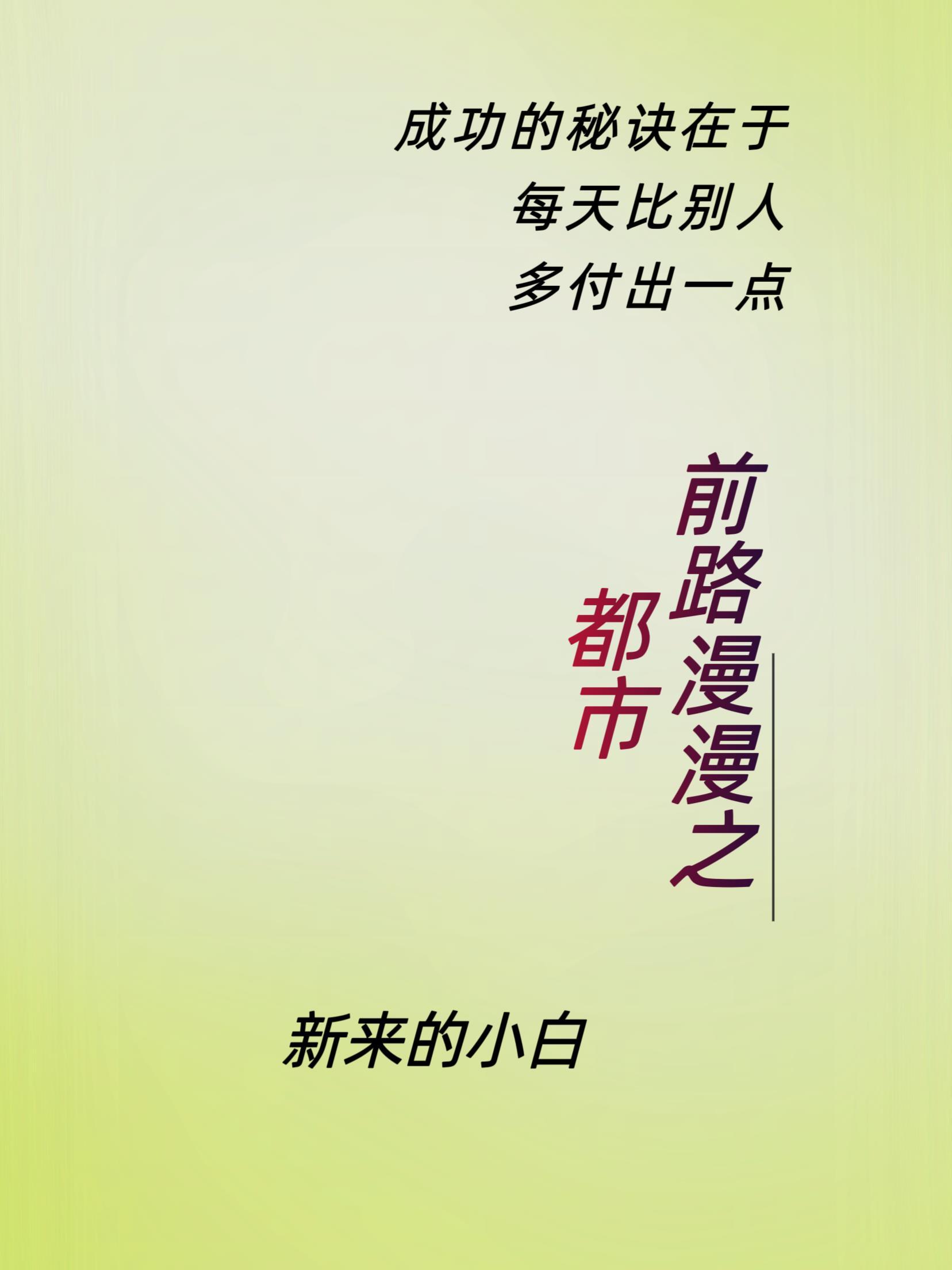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祝东风且共从容什么意思 > 03(第2页)
03(第2页)
迟漪回想今晚上山时,那台迈巴赫里匆匆一眼的半爿侧影,与眼前的逐步重叠。
那人的影子离她只剩咫尺,她不由站直身体,背脊延至脖颈挺如一条直线,月影花簇下,她目光澄亮直直望他。
这已是他们今晚的第二次对视。
那双湿漉的眼里盛着天边悬月。晚风一拂,她睫羽扑闪,像风掀过一层涟漪,要搅弄谁心池。
靳向东静看她片刻,小姑娘也一直没收目光,似要与他分一分胜负。
两人距离愈近了,呼吸间能嗅到他身上萦绕着似有若无的雪松香与沉香,这缕香令迟漪神思清醒起来,自己今晚似乎是有些过分的,频频在针对他。
但转念一想,自己尚有落在他手里的一枚把柄,迟漪斟酌着不情不愿开口“靳生,好巧。”
靳向东这些年常伴祖母沈嘉珍与母亲黎嬛左右,与女性相处时他总会习惯先掐烟,只是眼下这片庭院是作观赏的,周围这片区域并没有设烟灰缸与可以灭烟的白沙石,以至于他背在身后的左手指间还捻着那支燃了一半的烟。
捕捉到她眼里闪过的漠然,靳向东眸色微动,转了话题“知恒没陪在你身边”
迟漪是记仇的。靳知恒刚才总将话题往她身上引,令她想回避一些糟心问题都无计可施,出来透口气就是为了平复心情,此时又被他提起
迟漪细长的眉微不可查地一蹙,澄澈明亮的一双眼睛盛着疏离的笑,语调怪得很“今晚是你们的家宴,知恒哥哥按理也该多陪亲眷。”
哪能顾上她这外姓人。
是句句不提他,又句句直点他。
这脾气也不知是怎么娇惯出来的。
靳向东完全没有安慰如她这般年纪的小女孩的经验。
他生来是靳家长子,又是老爷子亲自培养的集团继承人,靳家没有妹妹敢在他跟前耍骄纵这一套,即便是明毓也懂得察言观色在他跟前撒一些无伤大雅的娇。
她们对他更多的是敬重、敬仰之情,远观而不敢冒进。
唯独迟漪,她一出现已是特例。
对他的针锋相对与阴阳怪气竟是藏也不肯藏,无畏无惧。
靳向东半垂眼睫,视线拂过她眼角残留的湿润,难道是哭了他有些无奈,拿出一方叠放整齐的丝巾递给她,语气郑重
“冬夜风寒,仔细着凉。”
月色素炼,目光交汇的一霎,迟漪只觉心尖有激流湍湍,她本以为今晚已经足够失礼,索性不管不顾将这份讨厌进行到底,却没想过他雅量过甚,毫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
又或者,贵重温雅如他,并不会因她这样如微尘般的人加以计较。
他们到底是不同的。
迟漪自认此战溃败,她力量微茫,气量也小,敌不过眼前人。
那些积攒在心腔里的气焰顷刻褪去,只剩泄气。迟漪眼里那些坚冰一样的锐气在消散,可即便如此,她也依然不想被他看轻看穿,只得欲盖弥彰地垂下眼帘,从他掌中接过丝巾,指腹轻轻擦过他温度,像被烫住一般又极快地紧攥丝巾收回手。
她咬唇,真丝在她手心如同蹂躏。
靳向东默不作声看她变换之快的神情动作,清楚她才是真的绵里藏针,又知进退,只是年纪太小,不懂如何收敛锋芒,只敢一昧冒进。
这样的人,倒不至于会对靳家有歪心思,她只是习惯保护自己。
靳向东虚应着一笑,向她略微颔,转身沿着这条冗长的汉白玉长廊离开。
庭院的灯火通明,将他背影刻画得矜贵落拓,令人觉得太过遥远。
迟漪掌心湿濡,越攥越紧时才察觉到丝巾里面应该包着什么,她浓黑睫毛颤了颤,有些茫然地将丝巾平展开,廊灯煌煌映亮眼前那条钴蓝色丝巾里裹着一枚打火机。
她的指腹用力在摩挲机身雕刻的藤蔓纹路。
他明知暗处窥伺者是她,也肯将东西物归原主。
可这样,又衬得她多么不识好歹。
迟漪在原地踯躅不前,须臾,有两束白茫茫的车灯自前方喷泉打过来,光源照过她逶迤的大幅裙摆,她抬起脸,入目便是那台挂三地牌照的迈巴赫62s。
夜色打破已久,她目光下落,提裙走上前。
驾驶座的依旧是德叔,他向来过目不忘,看清后视镜倒映的人影,回头提醒后座正半阖眼眸小憩的男人。
“外面站着的好像是那位迟小姐。”
靳向东眉间成川,摇下一截车窗,晦暗不明的一双漆眸隔半爿玻璃停留在她身上,他的确没料到迟漪非但没走反而上前。
于是他作壁上观,等她下一步。
这位置的灯光不明不暗,不会有暴露她情绪之虑。
迟漪犹疑半秒咬唇看过去,车内冷寂灯光下,那人身姿清举,端的是八风不动。
即便距离这样短,他也并无主动必要。
上位者总习惯如此。
迟漪再清楚不过,她止步檐下,亦不肯往前分毫。
夜色划过隆隆雷电,斜风细雨顷时飘落,一幕雨帘倏忽将他们隔分出一道透明界线。
夜雨声啁哳,也不知他是否有听清,迟漪挺直背,微垂眼帘看向车里人,落下清凌凌的一声
“还是要说一句,多谢你。”&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