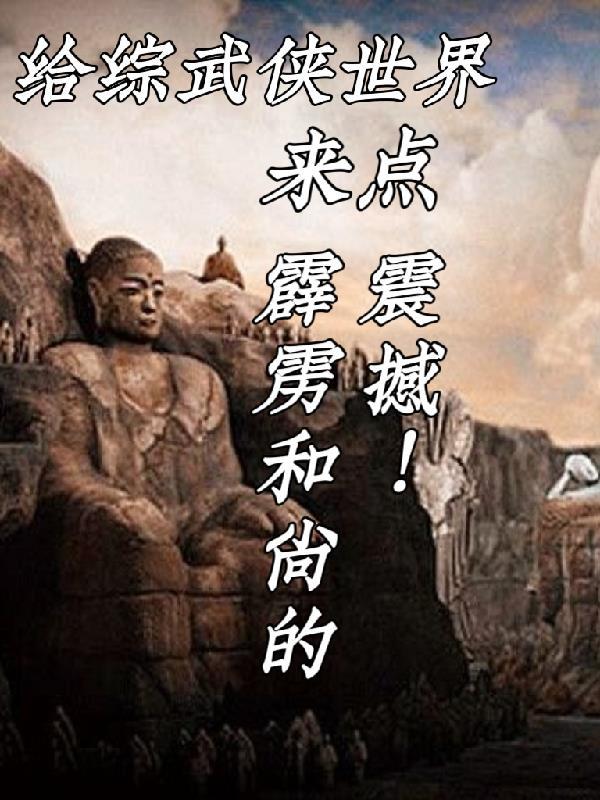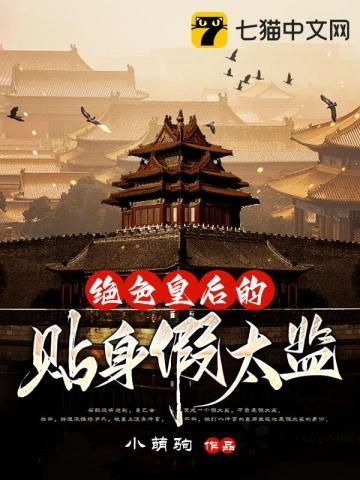凤阅居>焚香和青云打boss谁快 > 第15章 痛无言(第1页)
第15章 痛无言(第1页)
“她求我帮她杀了苏诫。”宿屿突然说,语气淡淡,给人以沉痛而无力的感觉。
“杀……”思归闻言怔愣。
良久后,才讶异地重问:“她求你帮她杀苏诫?你杀苏诫?她要杀苏诫也算在情理,毕竟是你先杀的她嘛,但这你杀你自己……”
思归瞧着眼前人,对他平静之下的惊涛骇浪视而鄙夷:
“恕在下愚钝,不能揣摩指挥使大人处世之精诡。还是老老实实当我悬壶济世的郎中吧!有些人呀,天生就爱作死,那就让他作吧。”
从袖袋掏出一白瓷药瓶,先喂宿屿服下两粒清续丹,将其衣服解了翻将过去,趴平,而后开始为爱作死之人推脉舒经。
宿屿的背宽健匀实却不壮硕,骨骼线条与肌肉薄厚都恰到好处的养眼,一点不像出现人前那样孱不胜衣。
肌肤也白净光滑,唯一扎眼的是,他的背部近肩的部位横亘着几道长短不一的伤痕。
那些伤疤色各深浅,像附在皮肉上吸血的虫子一样令人入目不适。
目测是不同时段遭受。
就观感而言,这样的伤实在丑陋,但之于男儿,它们却让眼下病弱如雨后桃花的“娇娘子”凭空增具几分英武之感。
宿屿侧过脸,看着泛黄的纸窗:“做下这个决定当初,我便预料到早晚要面对如此结果,我也曾反复预演过,若她真的要找我寻仇,我当以何种方式应对。”
“想过千般,思下万策,可当她决绝的对着我说出要杀‘我’时,我终究做不到心无波澜。”
思归道:“所以我说嘛,你就是个喜欢找死的人。为了一个女人,看你这几年过的什么日子!白天要去宫里应付姓夏的皇帝,完了还要赶回我这殓芳堂当你竹月深的宫主”
“是,她对你很重要,有家人之亲,有恋人之好,是你自己养大的想娶的妻,可是苏承谏,你也只是一个人,一个血肉之躯,与天下万千人一样,你这样折磨自己……累死你!”
语气从头至尾怨气深浓,恰有种恨子不成才的哀愁。
“我如此做不止为了她一人。”宿屿道。
“是是是,你不止是为了她好吧。你是为了天下人。你伟大,你了不起,你菩萨心肠,你就是嫌命太长。”
“让你来给我看伤,不是让你来拿话噎我的。”
“公子我是恨你不开窍。你说你,明明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关系又暧昧,何不就向她挑明了你的不得已,如此,你们还能相互携持,相互温暖,有什么事也有个倾吐的人,相亲相爱,多好,我都要嫉妒的”
“哪有那么简单。”宿屿叹气,“当初为了保住她用了那样极端的方式,怎能是两句解释即可抚平的。你不知道她‘死’在我手里时……”
喉咙忽然像被一把沙子卡住,“此前她每一回看见我,眼里总似装了星河日月,就算是受了委屈,落在我肩膀的眼泪都是坠海的星粒,但是那一天,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眼神是漆黑幽深的,比冥狱还森冷。”
“我当时就知道,我难了。我是压垮她最后一丝坚强的重石;是摘去她满天光彩的恶魔;是踏着她尸体上位的奸佞。”
说到此处,他闭上眼睛,陷入久久的沉息。
思归停手瞧了他一眼,到底什么也没说,默默按摩。
翻着白眼腹诽:“老天写得好好的一册甜得使人牙掉,令人嫉妒的情爱话本你要生生撕去关键几页,非亲自动手把神仙眷侣携手平山海的传奇改写成满目狗血的虐恋故事!活该你落到今日躺着不能反抗的境地!”
五年前,苏诫飞书殓星谷,求思归相见,说是十万火急的要命事。
思归火急火燎移驾彧国,一见面便受清朗如月的少年扑通一拜。
他当时急急慌慌,每一寸肌肤都紧绷得颤抖,每一根发丝都在焦灼。
问他发生了何事,他也不说,只问:“我要杀一个人,你能帮我救她吗?”
“你既要救她,为什么还要杀她?”
“她若不死在我手上,一定会死在别人手上,我想了诸多方法,觉得只有她“死”了才能更长久的保护她。你医术精绝,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苏诫攥着他的手,含泪乞求。
“只要你能救下她,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
“我是医者,做的是救死扶伤的高洁事,你拿命给我作甚?我稀罕?”
“那我给你钱,你不是爱华服美食嘛,我把此生攒的钱都给你好不好?”
思归深思了许久,给了那痴情种一粒“凝息丸”,说:“左心一寸,昏死前喂她服下此药,两个时辰内把人交给我,半月后来找我要人。记住,必须左心一寸,能不能救她,全看你手准不准。”
思归不知苏诫拿了药之后都做了什么,只知十一日后的一个傍晚,苏诫披着身黑袍出现在他房门外,当时雷雨交加,他把一条湿漉漉的马鞭交给他。
“一切已安排妥当,没有人会怀疑,马车就在门口,你将她带走吧,拜托了。”
苏诫看着好友驾上车,在漆黑雨幕中目送他离开。
风雨里,他的目光是那样呆滞,形容是那样落魄,像一只初来乍到的水鬼,湿乎乎的,外表看起来凶恶诡异,泪汪汪的眼里泛滥的全是迷茫之色。
他把比自身性命更重要的东西交托出去,留下一副凄凉的空壳在原地。
思归拿着特令连夜出城,戗雨疾驰,中途弃了车,换船南下,在伤者气息耗尽的最后时刻终于赶至殓星谷。
经历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手术,他如约救回了痴友的慕慕。
然而那姑娘心伤太重,即便是救回了她的命,她却已不愿回拢意识。
思归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能将池慕从失意中唤醒,最后不得不去信给苏诫,向其明言当中意外。
苏诫只用了五天时间便从大彧皇都赶到了北雍南境,看着容色鲜活却死气沉沉的姑娘,他大手一捞,当即就拎起了思归,质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不是说有把握医好他的心上人吗?
他指着思归的鼻子,骂他屠夫、庸医、凶手……
思归挣开伤患亲属,极不服气地说自己确实将人救回来了,伤者不愿醒不是因为身上的伤,而是因为心上的伤。
苏诫听了之后,瘫坐在地,哭成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