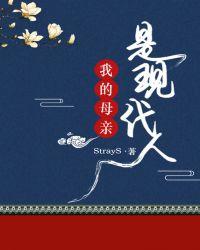凤阅居>东原陈涵 > 第78章(第1页)
第78章(第1页)
那人,不,应该说将她压在榻上,摘下面具的那人,并不是长安。
此事煞是诡异,令景晨根本理不清思绪。
“我晓得。”长安面色如常,抬眼间,景晨看见她淡青的衣衫下微红的痕迹,思及那可能是什么,景晨脸色突变,连忙后退了半步,几乎不做犹豫地冲着坐着的长安行礼。
“作甚?”长安不解,她抬着手,制止景晨的行礼。
好端端地行礼做什么?
景晨的面色冷得紧,也不说话,只是悄悄地瞧着长安的肩头,还有细长的脖颈之上淡红色的痕迹。
摸了摸自己的脖颈,长安叹了口气,拍了拍景晨的胳膊,说道:“问筝还不知,这只是一场幻境吗?”
幻境?
景晨的眼眸眨了眨,一脸的难以置信。
“自然是幻境。”长安站起身,她抱着肩,斜了景晨一眼,随后像是忽然明悟了一般,道,“难不成问筝当真欲同我欢好?还是说,问筝确是女子?”
她这样说,景晨才恍然发觉自己未在长安面前遮掩自己的性别,方才竟然将遮面的面具都摘下了。她的面容一旦被人看见,哪里还能有人认为她是男子。
“问筝莫慌。”长安的眼眸中满是笑意,她上前,肩头抵着景晨,笑着说,“既是幻境,那自然许多事都做不得真的,你说可是这个道理?”
许多事做不得真?
景晨在心头暗自念着这句话,思考着长安所说的是什么事。她下意识地抬眼看向长安,恰在此刻长安的目光也在她的身上,四目相接,景晨忽的明悟。
欢好吗?
那自是做不得真的。
“好生收着此方面具吧。”长安忽然说道。
景晨一愣,还未反应过来其中含义,就见长安衣袂飘飘,不知何时近前的窗户竟被打开,夜风涌入,吹动她的衣衫。
她的目光一直在长安的身上,长安看向她片刻后,转过了头,墨色的眼眸往天边的圆月看去。她的发丝散落,衣衫也算不得多么规整,就连唇边也挂着不应属于现下身份的笑容,可莫名的,景晨喜欢这模样的长安。
“你可知晓我的名姓?”
自是不知的。
她是千金之躯,整片神州大地,世人只知晓她的封号。
长安立在原地,一脸安静,她的眼眸里泛着光,似是天边闪烁的星辰般。她抚上景晨的面,垂首轻笑。
“你个呆子。”
一双黝黑的双眼,蒙着的那层纱终于散开,显露出内里的光彩。
外面不知何时又下起雨来,狂风敲打着窗户,一道雷劈下。景晨立即反应过来,她正欲抬手掩住长安的双耳,却恍然发觉,方才还在自己面前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雨水吹入殿中,近乎扑在景晨的面上,风雨太大,她立在原地,看向长安消失的地方,双腿一软,竟直接跪倒在地。
随后,她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之中。
司龄
司龄
景晨的意识算不得清醒,就是身子也开始滚烫发热,她仿佛置身于一片虚空之地。此地荒无人烟,就连那本应该高悬于上的明月,现在都如银盘一般摆在她的面前。
这月实在是太大,太近。
好似,她真的悬于空中,即将奔向明月。
立在原地,景晨呆愣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圆月,今日的许多事情实在过于光怪陆离,远超她的认知。她望着圆月,不知过了多久,她忽然感觉到身侧站了一人。
偏头望去。
红色大袍的女子同她并肩而立,她双脚悬于空中,手中还拿着一把长剑。这女子的面向极为好看,模样看起来也就二十余岁,唯独她的眼眸太过深邃,不过一眼,景晨便有被看穿的感觉。
“晨,见过司龄大人。”
景晨是识得女子的身份的。
雾灵山的大祭司——司龄。从幼时被母亲送上山时,司龄大人便是如今模样,现在,她仍如同过往那般。好似岁月从未在她的身上流淌而过,而这十余年对她来说,也不过是漫长人生中苍渺的一瞬。
司龄的眼眸笼着一层看不清的思绪,这十余年她自然不是第一次受景晨的礼,唯独此刻,她竟冲着景晨回了一礼。在她低头的一瞬,景晨敏锐地发现,她的眼眸竟不知何时变成了金瞳。
怎的?
怎么会?
忽的,她的脑海里像是被人狠狠地敲击了一下,猛然想到方才,方才长安的眼眸……
景晨定定地盯着司龄的金色瞳孔,司龄泰然自若,她的眼眸深沉至极,似是要将景晨吸入一般。
“晨不解,还望大人解惑。”景晨困惑至极,她的眼睛被司龄盯得很痛,迫使她不得不抬起一只手捂着自己的眼睛,开口道,“方才晨在殿中瞧见了一人,还和她有了些许交谈。晨想知这是大人所布的幻境,还是晨无端生出了梦魇。”
司龄见状,拂袖一挥,本高高悬挂于上方的明月消散。不多时,竟出现了一座草庐。不过这草庐同景晨见过的一般草庐不大相似,虽都是看着质朴的,但眼前的草庐可比一般的草庐高大了太多太多。
随着司龄的脚步,景晨一同进入草庐。
草庐内部空旷,只有两把椅子,司龄率先坐下,抬手示意景晨也一同落座。
景晨坐好,仔细听着外头还有呼啸的风声,有一缕细碎的风吹了进来,不知怎的,直奔景晨而来。她面上的面具并不能遮掩住这缕风,风直接吹到她的眼睛上,令她的眼睛涩涩的,很是不舒服,眼泪作势就要流下来。
恍惚中,司龄开口了,她说道:“将面具摘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