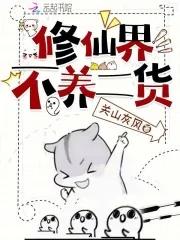凤阅居>在逃女主我不会再爱你 > 第48章(第1页)
第48章(第1页)
杜宣缘笑眯眯看着他吃东西,很是心满意足的模样。
就是视线太专注,叫陈仲因不动神色地往旁边挪着,没多会儿便只留半张侧面在杜宣缘眼前。
杜宣缘也不在意,她悠哉游哉坐在床边,忽然长叹一声,道:“唉,你们陈家怎么这么多讨打的人?一个一个送上门来,打得我手疼。”
陈仲因默然片刻,咽下口中的食物,道:“下次你应该没法动手。”
杜宣缘闻言眉峰一挑,道:“怎么?下回你亲爹要来?”
她这时候心情还不错,只笑吟吟想着:小陈太医啊,正吃着我投喂的东西呢,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
安排
不待陈仲因回答,杜宣缘又紧跟着嗤笑一声,道:“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你爹也出口些我不爱听的东西,我可不管那是谁,照打不误。”
“不是。”陈仲因却摇摇头,放下手中的半块米糕,一本正经地看着杜宣缘道,“我觉得下次他们绝对不会‘单打独斗’,应该会纠集一伙人上门同你‘讲道理’,你打不过来的。”
不是“打不过”,而是“打不过来”,人太多,一个一个打过去怎么打得过来?
杜宣缘愣了一下,随后猛然笑出声来,并愈演愈烈,演变成前仰后合的哈哈大笑,看得陈仲因直担心她一口气没跑对笑岔了气。
陈仲因又很疑惑她为什么发笑,专心致志地看着她。
好半天杜宣缘才抹去眼角笑出来的泪水,直起身子凑到陈仲因面前,眉眼弯弯道:“言之有理,下次他们一大群人过来,我哪里打得过来呀。”
听到杜宣缘说着买几个奴仆帮忙的话,他低头继续啃着米糕。
杜宣缘突然问:“小陈太医,若是我打不过来,你会不会上来帮我?”
陈仲因摇摇头,道:“君子动口不动手。”
杜宣缘盯了他好一会儿,突然伸手在他沾上米糕碎屑的嘴唇上使劲揉了揉,继而随性道:“免了,你这讷口少言的,指望你为我说句话都要等得我须发皆白,你还是乖乖待在屋里吧。”
陈仲因想说他今日龟缩不出,是因为杜宣缘身份特殊,此地皇城脚下,他不敢作赌。
可他盯着手里的米糕看了好一会儿,终于还是把解释的话连同食物一起咽下去,在自己的腹中慢慢消化。
过了一会儿,杜宣缘又问:“晚上想吃些什么?我一会儿出门,回来时带给你。”
陈仲因摇头,道:“夜中吃得多容易积食,对身体不好。”
他这也是想劝杜宣缘晚上出去不要大鱼大肉地吃,可他不知道杜宣缘有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眼见着杜宣缘只是朝自己摆摆手,人已经起身准备离开,陈仲因张张嘴,终于在她临出门前发了声,道:“夜间少食些油腻辛辣之物,路上注意安全。”
杜宣缘回身朝他应了句,继而离开。
陈仲因低头看向有些皱巴巴的空油纸,觉得自己好像又把事情搞糟了。
。
杜宣缘同张封业去到牙婆处,参考着张封业的意见买下两男两女,又去市场里请了一位厨娘,给了他们住址,让他们自个儿找过去。
随后她去到迎南坊。
张封业不明所以,跟着杜宣缘七拐八拐,走进一个狭窄的巷子里,抬头瞧见一个小姑娘正在往外倒水。
小姑娘看见来人,愣在原地,像是在回忆什么,接着笑起来,对杜宣缘道:“大夫哥哥,你怎么来了?”
她看了一眼张封业,面露疑惑,又看向杜宣缘,迟疑着问:“这位是?”
“是我的朋友。”杜宣缘道,“也是你哥哥的同僚。”
接着杜宣缘面露悲切,道:“你的哥哥在太医院犯了事情,被关进牢中,他走之前嘱咐我照顾你们。”
阿春一惊,手中的木盆也端不住,摔在地上。
张封业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杜宣缘对一个小姑娘坑蒙拐骗。
他虽然不清楚内情,但史同满与“陈仲因”绝不会是托付家人的生死之交,但瞧见一屋子的小孩,他们失去大人庇护,在这皇城里还不知前路如何。
张封业不知何时对杜宣缘的人品产生了迷之自信,觉得她一定是个正直的好人,是真心诚意想照顾史同满的弟弟妹妹们。
若是叫杜宣缘来评价,她一定会觉得整个太医院里最好骗的是史同满,其次便是张封业,看着也是精明的模样,但不知为何格外好糊弄,似乎他虚长的那些年岁都用在跟亲爹对着干上。
“史兄也是受奸人所惑。”杜宣缘抿了一口热水,也没嫌弃这茶杯豁口,将它捧在手中,继续道,“我受他所托,定然要好好照顾你们。你们若不嫌弃,暂住我宅可好?”
除了阿春,狭小的房子里还挤着五个孩子,他们像一窝小鸡仔,缩在一起怯生生看向杜宣缘。
他们没有什么主心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个嘴巴跟摆设似的不敢张嘴说话。
这群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便是阿春,史同满在太医院当值,时常几天不回家,家里事情也多是阿春来处理,此时此刻那些孩子们便将目光投向最大的姊姊。
阿春低着头,不知是为自己锒铛入狱的兄长,还是为他们五个孩子未知的前途忧虑。
片刻后,她抬头望向杜宣缘,杏眼里满是明亮的星子,像是某种希冀,她对杜宣缘道:“谢谢大夫哥哥愿意收留我们……”
一锤定音,毕竟他们确实无处可去。
。
陈仲因正窝在房间里看书。
杜宣缘将他放在太医院谨行所的房间里的那些手札、抄录带出来不少,陈仲因闲来无事便将这些总结的经验翻出来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