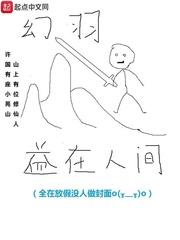凤阅居>呕吐袋骨科TXT百度 > 100我也很难的呀妈妈(第3页)
100我也很难的呀妈妈(第3页)
裴琳面容扭曲了一瞬:“你还敢告诉别人?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以为你不是你爸爸亲生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前四十年和别人有一腿,裴音,你哥哥在你心里已经比妈妈的尊严都重要了吗?”
裴音没想过这件事,呆了呆,结结巴巴地自证:“我爱妈妈呀,怎么会……这是两件事呀,林铭泽人挺好的,怎么会那么理解呢?或者,他最多以为,妈妈是有苦衷的……”
裴琳忍无可忍,颤声道:“李承樱!你看清楚过你现在的名字没有?我的苦衷…我的苦衷就是我女儿被亲哥哥搞到格伢?”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突然来到裴音跟前,推了她一下。
从前母女相依为命,裴琳常用方言叫裴音的名字。后来到春喜生活,也偶尔唱几吴语歌哄她睡觉。
这是第一次裴琳用吴语叫她的新名字。
“李承樱……李承袂李承樱,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兄妹的名字,你护照身份证学生证上的名字,已经不是裴音两个字了!你就该谢谢李承袂到哪儿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个安静地方把你带去过夜,否则你们去开个房登记都要遭人家白眼的!更别说是……更别说是上床,李承袂那个人模狗样的禽兽……”
女人说得急了,停了停,才道:“金金啊,你有没有想过这说出去,人家真的会觉得你不要脸的。你就没有为你的脸面努力过一点点!”
裴音被说懵了,她浑身都在抖,那些字眼李承袂最火大的时候也没对她说过,听得耳朵痛。
她有些呼吸艰难,捂着腔口剧烈喘息,在缓过气后的某一刻,突然哭了出来: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了?难道是我想这样的吗?妈妈有没有想过,成年礼那天,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变得跟李承袂三个字几乎一模一样,我是什么感觉呢?本来可以不用这样的,我不改名字,白纸黑字哪怕两个人的名字写上去,也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兄妹。”
她边哭边说:“如果……如果妈妈不非要嫁进来,说不定我可以和他结婚的,我可以用裴音的名字和他领结婚证……我过十八岁生日那天,妈妈在宴会上那么高兴,可我不是的,我用了好久才接受这个名字,妈妈却用这个名字骂我不要脸。”
裴音捂着眼睛哭的满脸是泪,手指也起抖来:“妈妈,我也很难的呀…我真的…我真的喜欢他呀……”
裴琳最听不得“喜欢”二字,闻言彻底动怒,指着她道:“什么喜欢?你说的劳什子喜欢,就是在十八岁去爬亲哥哥的床吗?那是你板上钉钉的亲哥哥。谁不行,那个林家的小孩子不行吗?你什么疯要去爬李承袂的床,就喜欢离过婚结婚两年连孩子都不生的吗?”
她看着裴音苍白的脸色,又记起李承袂对此事的坦然态度,泄愤般地骂了一句:“贱东西。”
这些话终于能诉之于口,裴琳感到畅快。教训女儿比教训继子容易得多,心理上她未必真的不见得他们在一起,但乱伦从来都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在态度上她总要拿出反对的姿态。
正垂头平复心情,思考后续的办法,裴琳就听到女儿的声音。她抬起头,看到裴音双眼哭得红肿,人却一反常态,直勾勾地盯着她。
“妈妈就很清白吗?”裴音攥紧了手,轻声道:“我和哥哥在一起,没有切身伤害任何人。可爸爸妈妈伤害的,明明不止一个人。况且如果真的要保护我,不应该在一知道这件事就去找哥哥‘算账’吗,去年除夕那天,我在和哥哥吵架,那天我们还接了吻,妈妈但凡真的关心我,会一点都没察觉吗?”
说到这里,女儿的嘴还没停下,在说更让裴琳无法忍受的话。
偏偏她知道她说的是对的。 “明明你也不清白,”女儿直直望进她的眼睛,声音甚至轻快起来:“就是因为你不清白,你和爸爸……你们伤害了别的姨姨,连同姨姨的小孩一起,他才会选择伤害我呀。”
母女都被彼此逼到绝境,所幸她是妈妈,总能压她一头。
不知是心虚还是暴怒,总之在短暂的几秒沉默过后,裴琳突然几步上前,抬起手就要给裴音一个巴掌。
手才抬起来,反锁的门已经被踹开。
李承袂面若冰霜大步走入,抓紧裴琳的手腕甩开,把裴音护在怀里。
“我不干预母女谈话,不介意你当着我的面反锁房间,不是为了让你跟她动手的。
“她做错的事,很久以前已经为此挨过巴掌,不需要再挨了。”
李承袂牵住裴音的手。
女孩子的手心全是眼泪和指甲掐过留下的痕迹,湿漉漉的一按一个白印,映着指甲押出的粉红色月牙,可怜得几乎有些可恨了。
他俯身观察妹妹的状态,见裴音肿着核桃一样的眼睛怯怯望着他,像是怕他听到刚才的对话生她的气,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受。
林铭泽也好,林照迎也好,都是外人,他有的是办法给她出气。
可这是她妈妈,照她那记吃不记打的绵软性子,大概用不了几天就要重新叫着姆妈亲近裴琳。他再动怒,也只能在保持理智的情况下出言警告,或者,做他一直想做的事——
李承袂收紧怀抱,当着女人的面,垂吻了吻怀里裴音被眼泪弄湿的额头。
他低声道:“想吃消夜吗?我带你出去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