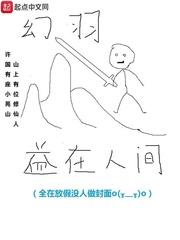凤阅居>主角他怎么还是变偏执了by > 第98页(第1页)
第98页(第1页)
一句不轻不重的疑惑,让他就那么收了声。他默然坐下,也不出去了,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但由于他身体越来越虚弱,食不知味,吃两口就吃不下了,没多久就放下筷子。
景容仍旧淡淡的:“再吃一碗。”
他在言语里会去要求他怎么做,不吃就命令他吃,不喝就命令他喝,不想走动就命令他走动。
但巫苏真的吃不下了,他试图让景容理解他:“我不太舒服……”
景容却还是淡淡地道:“再吃一碗。”
巫苏:“……”
巫苏:“……是。”
景容的气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强到这种程度的,巫苏并不清楚。他只知道跟景容在一起相处的每一刻,都令他窒息。
一个温故,一个景容,这两个人不知道在搞什么,紧着他一个人折磨。
而他也确实被折磨到了。
他焦虑,痛苦,终日惶恐不安,还身体不适,这比死了还难受。
而温故也并不是失踪了,而是走了,就在巫家到的那天。他醒来后就问巫长老要了匹马,说要出去,后来看着那匹马,他忽然想起自己还不太会骑,于是转头要了辆不错的马车。
巫长老先是试图不让他走,后又提议要跟着去,不管是哪个,温故都没同意。
温故接过缰绳,对着马车一跃而上的时候,巫长老不断地叹气:“少主可要早些回来啊!礼宴之前定要回来!不然赶不上第二天去西山了!”
温故:“嗯嗯嗯。”
他应得挺好的,但那样子实在不像会乖乖回来。
“巫苏”是巫家少主这件事,很快就在景家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正版巫苏是从林朝生嘴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只要巫家人一到,这个身份就瞒不住,所以巫苏一点都不意外,林朝生感叹了一番那小子竟然是巫家少主,然后才道:“不过他走了。”
巫苏惊得浑身开始炸毛:“走了?去哪儿了?”
林朝生摇摇头:“不知道,反正好像走得挺急的,就像是逃走了一样。”
一说起这个,林朝生就有话说了,笑道:“你说会不会是他发现打不过咱们少主,吓得连冬炼都不参加了?”
看着笑意越来越大的林朝生,巫苏心里的恐惧也越来越大。
他觉得温故是真的会走的那种人。是真的走了就不会回来的那种人。
但他还是像之前一样,雷打不动地找寻禁术,他一直以为那是他唯一的出路。
藏书阁每一层的环形阶梯之间相隔两人高,书架嵌在其间,上面摆满了各种藏书。因书架过高,无法取到位于上方的藏书卷轴,所以便用到了梯子。这样一来,要找到禁术相关书籍,还要从中找出破解之法,就变得难上加难。
巫苏一直在很努力地找,可找到现在,跟禁术相关的,那是一本没见过。他摸出一本书,瞅了眼又放回去,然后再摸出另一本书,如此往复。
在不需要动脑的情况下,他抽出来看一眼再放回去,几乎全凭肌肉记忆,那不需要用到的脑子就渐渐陷入了一种放空的冥想之中,这样持续着不知过了多久,他的手摸到一本书,然后再没把它抽出来。
禁术是不完善的,即便找到了施术过程,知道所需的各种条件,也不见得能堪破玄机。
因为那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脑中一开始没能意识到的那种不对劲,在这一刻,被他抓住了点东西。他突然意识到,温故在骗他。
温故在极短的时间内,编了个近乎完美的理由,就让他一头栽进了藏书阁。
而问题的关键是,他信了。
不光信了,还深信不疑。
因为他不觉得温故有骗他的必要,就像他没有骗温故一样。
可是温故还是骗他了,他收回手,从梯子上爬下来,然后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书海,他想不明白,温故为什么要把他骗来藏书阁。
垂下眼,视线渐渐移向大厅正中间那个闭眼小憩的身影,他有了点不好的预感。
这些时日相处下来,他已经被景容搞得神经衰弱,而温故呢?温故跟景容相处的时间更久,恐怕是早就想逃了!
所以才故意扯出个什么藏书阁,以找出禁术为幌子,把他留在景容身边。
这样的话,温故就有充分的时间逃离,等到时机成熟,也就是恢复巫家少主身份之时,借机彻底离开景容的掌控。
这副身体没有灵根,在修仙界,没有灵根就没有一切发言权。而看景容那样子,也完全没发现身体里面换了人。更何况,他本就在这副身体里待了十多年,就算他说他不是,恐怕也没人会信了。
所以他只能咬牙认下这个身份,从此一生都在景容的囚禁之下活着。
他咬紧牙,紧握拳头,心中愤恨不已。
温故……你可真行啊!我早晚要杀了你这个伪君子!
身体上的疲惫感日渐加重,就这么会儿时间,他已经完全站不住了。
扶着楼梯扶手,他吃力地走下去,想去榻上坐着休息一会,再是不想面对景容,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只能去。
他在榻上闭眼摊了会儿,然后直了直身体,正想喝杯水,无端端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在盯着自己,还有一种没由来的阴寒感。
他浑身僵硬起来,没有转过脸,只将眼珠子往景容那边一点、一点地移过去。
天已经黑了,烛台上亮着烛火,将两人包裹在朦胧的光芒里,映着景容冷恹又惨白的脸。
只见景容侧靠在一端,波澜无惊地睨着他,眼眸又黑又空洞,好似深渊一般,仿佛多看一眼就会被摄去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