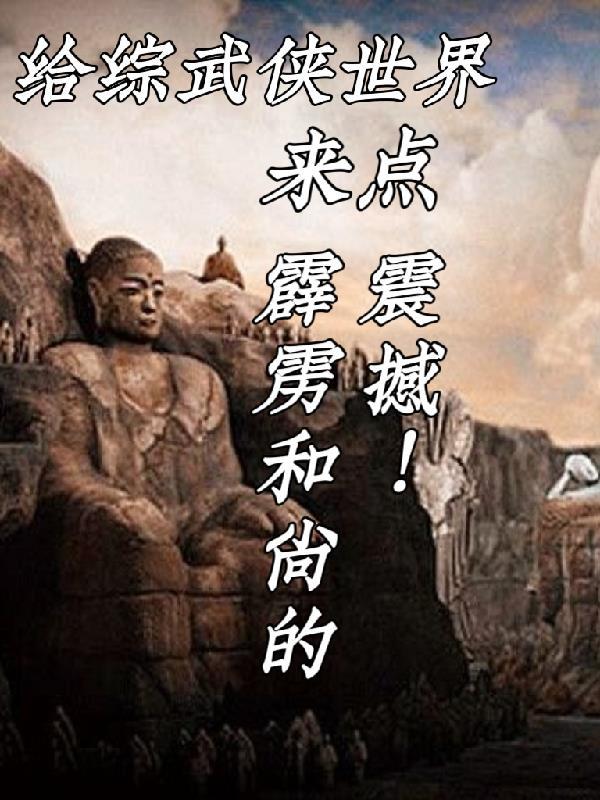凤阅居>何须浅碧深红色暗示什么爱情 > 家族故事中的审父与自审以及革命的沉思(第1页)
家族故事中的审父与自审以及革命的沉思(第1页)
家族故事中的审父与自审以及革命的沉思
与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拥有坚定的宗教信仰相比较,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就是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心理。正是在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牢固家庭或家族观念的基础上,中国文学史上才会出现一系列可以称为“家族小说”的优秀文学作品。家族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在从古至今的文学史上真正称得上是蔚为大观、硕果累累,现在,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也加入了这一文学行列之中。关键的问题是,与此前的这些家族小说相比较,邵丽的《金枝》到底增加了什么新的思想艺术因素?
在小说下部的第十三节,已经拥有了作家身份的周语同的女儿林树苗,围绕自己的小说创作,与周鹏程的媳妇胡楠之间,发生过这样一次饶有趣味的对话。胡楠说:“我看你写的小说里,有这个家族的影子。你是想全方位探索这个家庭吗?”面对胡楠的提问,林树苗给出的回应是:“这个家庭的复杂程度,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全方位地描述。但是,我怀念我的姥爷,我真是想多写写他。其实讲真的,把他写出来了,也就基本上说清楚了这个家族。他留给这个家族的是一个背影,在每一个家族成员眼里都是不同的人设。我妈妈、鹏程的妈妈,包括我的舅舅们,甚至周家的这些亲戚,他们每个人叙述的我姥爷都不一样。我想了解姥爷的过去和现在,然后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我想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姥爷的纪念。”虽然是巧妙地借助人物之间的对话在谈论林树苗的小说创作,但明眼人马上就可以敏感意识到,胡楠和林树苗所具体谈论的这个以林树苗姥爷为核心人物的小说作品,正是邵丽的长篇小说《金枝》。在一部虚构的长篇小说中,由相关人物出面谈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理念与过程,正是西方现代小说理论中的所谓“元小说”手法。如果我们把《金枝》视为林树苗的家族故事完成品,那么,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身份错位。依照某种不成文的惯例,在一部小说作品中,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往往会是写作者的化身。但在《金枝》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却被设定为林树苗的母亲周语同。既然林树苗在小说中不仅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且还寻找各种机会大肆谈论自己写作的家族故事作品,那为什么不在文本中干脆把林树苗设定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呢?另外一个随之而出的问题就是,假如说文本中的若干人物身上会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存在,那么,这个人物到底是周语同,还是林树苗?又或者两个女性人物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晃动着邵丽的身影?尽管说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我们实际上都无法给出,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本身,却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把握邵丽的这部长篇小说。
既然是一部以林树苗的姥爷为核心人物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又会被命名为“金枝”呢?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除了林树苗的姥爷周启明,活跃于文本中的其他人物,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女性。邵丽用“金枝”一词,喻指小说中的一众女性人物,是无可置疑的一种文本事实。
在具体展开对这部作品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小说的叙事方式。整部《金枝》共分为上、下两部,各以八节的篇幅而平分秋色。上、下部之间的分界线,是周语同父亲周启明的死亡。上部主要讲述周启明生前的家族故事,下部则集中聚焦于周启明去世后家族后代的故事。因此,如果说《金枝》所集中讲述的是上周村周氏家族前后三代人的故事,那作为中间一代的周语同所承担的,就是三代人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扭结作用。正如同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倘若没有她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家族荣誉感的关键性人物存在,上周村的周氏家族,就极有可能是一盘散沙。从这个角度来说,把周语同设定为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自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邵丽在《金枝》中并没有让周语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贯穿文本始终。一方面,我们当然应该承认每一位作家都拥有选择设定叙事方式的自主权利,但在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坦承,在阅读《金枝》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周语同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的那些部分。虽然说在一部长篇小说文本中采用多种叙事方式,在当下时代的写作实践中,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我却不无固执地认为,具体到邵丽的这部《金枝》,如果作家能够克服明显存在着的叙事难度,以周语同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来贯穿统摄全篇,那么,小说所最终获得的思想艺术效果可能会更加突出。
正如同林树苗宣称的将会把自己的姥爷周启明设定为整个家族故事中的核心人物那样,读完《金枝》后,给读者留下印象最为深刻者,同样是周启明这个人物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家的“审父”意图,也正是凭借女儿周语同眼中的周启明形象而得以最终完成的。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周启明,之所以执意要离家出走,是为了反抗奶奶给他包办的婚姻。因为心里不愿意,周启明甚至坚决拒绝以新郎的身份去接新娘穗子过门,奶奶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让自家收留的养孙周庆凡代替周启明前去迎亲。尽管按照奶奶的吩咐,周启明非常勉强地和穗子拜了堂,但在拜完堂之后,他才发现奶奶说话并不算数,“哪里是磕几个头就了的事儿?他被她关在新房里锁了半个月,酒肉饭菜都是用托盘从窗口送进去的”。被莫名其妙地关起来还不算,要命的是,就在这半个月期间,他竟然稀里糊涂地和穗子成就了一番好事。如此一种“成就”的最终结果,就是后来女儿周拴妮的出生。当然,等到周拴妮出生的时候,生父周启明早已“逃之夭夭”了。一方面出于对婚姻的恐惧,另一方面又怕回到县城的学校后遭到同学的耻笑,十五岁的少年周启明便离家出走,去找爷爷周同尧了。由于离家出走参加革命之后打开了眼界,接受了现代生活理念,早在结识后来的妻子朱珠之前,周启明就写信回家给奶奶,主动提出要和当年包办婚姻的妻子穗子离婚。面对着孙子的离婚要求,已经守了一辈子活寡的奶奶,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规劝孙媳妇穗子面对残酷现实,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早日另找人家改嫁。没想到穗子竟然也是个死心眼的从一而终者,尽管办了离婚文书,她却仍然坚持离婚不离家。这样一来,依照传统的习俗,“在上周村,穗子还是周启明的媳妇”。虽然穗子留在周家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一种选择,但明明曾经有过丈夫,到最后却被丈夫活生生抛却这一残酷事实,使得穗子的心态在不经意之间被扭曲了。这一点,尤其是在周家祖母去世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祖母在丈夫就在,她是祖母做主娶回来的,与其说她是嫁给了丈夫,还不如说是嫁给了祖母——只有祖母能确定她的身份。祖母便是她的人生戏台,戏台塌了,她再也演不成个角儿。她任着自己的性子过活,在愈积愈多的怨恨里,一日日地刁蛮起来。”比如,她不仅坚持要把自己唯一的女儿命名为拴妮子,而且还悍然剥夺了她读书接受教育的权利:“她觉得读书才会使人学坏,才会跑出去不回来。周家三代媳妇都守寡,还不是跟她们的男人读书有关系?”大约也只有如同穗子这样的没有见识者才会以如此一种逻辑去思考问题。更关键的问题是,自打祖母去世失去可以依傍的精神靠山后,心态严重失衡的穗子干脆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怨妇:“整天骂天骂地,好像谁都欠着她似的。她的生命空间也越来越小,满世界只有自己的女儿拴妮子了,她是她活着的理由。”令人难以理解之处在于,一方面,女儿拴妮子固然是她的救命稻草,但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她却又在令人难以置信地折磨着拴妮子:“她常常把拴妮子身上掐得紫一块青一块的。她责骂她,为什么你不托生个儿呢?然后又搂着她哭,说,苦命的儿啊!”拼命地虐待唯一的女儿拴妮子倒也还罢了,更加变态的一点是,虽然在素日里她会把周启明骂个半死,然而,诚所谓“一物降一物”,一旦周启明真的回到上周村的时候,她却又会变得特别安静:“穗子倒也奇怪,整天价骂天骂地、千刀万剐地诅咒的人回来了,她却匆忙地躲到自己的屋里,不哭不闹,也不让拴妮子去跟他闹。”将以上这些相关的细节整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说着墨并不算多,但穗子这样一个精神内涵特别丰富的女性形象,已经生动活泼地跃然纸上了。单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穗子这一女性形象,既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也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王蒙《活动变人形》里的静珍,以及铁凝《玫瑰门》里的司猗纹这几位现当代文学中经典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