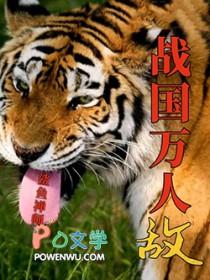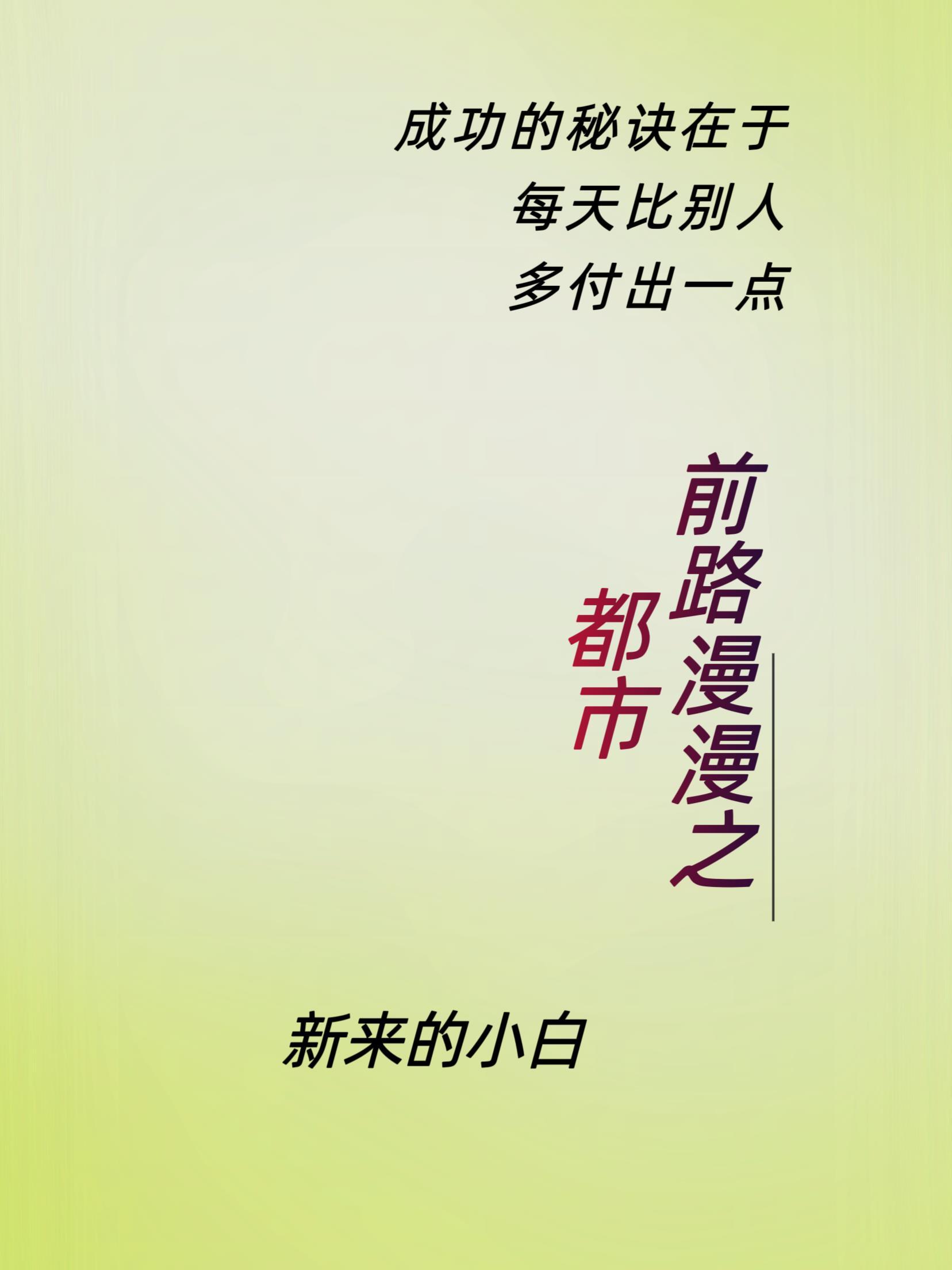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揽流光全文免费阅读 > 第101章(第1页)
第101章(第1页)
牧平也抬了抬手示意她发问。
“你是谁?”
牧平也看着她的眼神,那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洞悉与了然,他知道在这样的人眼前自己的一切谎言像会被毫不留情地戳穿。
“我姓顾,我的父亲是顾江临。”
裴雨眠闻言眼神有了奇妙的变化,嘴角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原来你是顾江临的儿子。”
……
薛容玦第二日便回了薛府,许是她身体的底子太差,许是昨日和桓帝的较量太累及心神,不论因为什么,白日里刚回来,晚饭后又发起了高热。
薛容玦已然习惯了自己这时不时生病的身子,可月红急得眼泪直掉,手上为她换上凉帕子,抽抽噎噎地道:“郡主,不然还是告诉将军和夫人吧?去请太医来?”
薛容玦自知不过一场小病,却又不想让家人为自己担心,想了想对如筠道:“乌淮巷有一家故念医馆,你去请大夫来,她叫茵陈,你就说是我请她来的。”
月红闻言抹了抹眼泪:“对对对,请茵陈姑娘,快快快,如筠快!”
如筠向薛容玦一抱拳,迅速转身离去。
薛容玦的意识模糊不清,昏昏沉沉间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是被月红晃醒的:“郡主,快醒醒。”
“啊…?”她朦朦胧胧地睁开眼,昏暗的烛光下,只看得到几个来来回回一定的身影。
茵陈坐在她身后扶着她靠在自己身上,薛容玦这才认出来是茵陈,虚弱地道:“茵陈姐姐,又麻烦你了…”
茵陈笑着摇摇头,示意月红快来喂药。
太苦了,她每喝一口都是煎熬,眉头紧蹙,终于喝完时她已出了一身的汗。
茵陈轻轻把她放平,轻柔地为她盖好被子,语气温柔:“睡罢,一觉睡醒就好了。”
她的声音温柔又飘逸,薛容玦缓缓睡去。
薛容玦醒来时除了感觉手脚有些无力外,竟然觉得有几分神清气爽,毕竟她很久没有如此畅快地酣睡一场了。
月红推门而入时就见薛容玦正扶着床沿试图下床,她连忙放下手中的粥快步前来扶她,言语中是掩不住的快乐:“茵陈姑娘真是厉害,她说郡主该醒了让我把煨着的粥拿进来,果真郡主就醒了。”
薛容玦笑了笑,脚步有些虚浮,坐在桌边一口口喝着粥:“茵陈和如筠呢?”
月红笑着道:“昨夜茵陈姑娘和如筠守了郡主一晚上,让奴婢去休息,奴婢刚让她们俩去歇着了。”
月红看她的粥喝得差不多了,扬声叫外间的小婢女把汤药拿进来:“茵陈姑娘说郡主喝完粥后把药喝了,之后要仔细将养着。”
薛容玦看着黑乎乎的汤药叹了口气:“真是不想喝,太苦了。”
月红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了几颗蜜饯,哄道:“郡主不怕,蜜饯很甜的。”
薛容玦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一口闷了汤药,结果因为喝得太急呛到了自己,咳了半天,一张白净的小脸咳得通红。
月红手忙脚乱地为她倒了杯水,她喝了水又吃了几颗蜜饯才把干呕的感觉压下去。
她虚弱地拉着月红:“我想沐浴,昨夜发了一夜的汗,浑身黏哒哒的,不舒服。”
月红拍了拍她的手:“郡主放心,奴婢知道郡主醒来定要沐浴的,都已准备好了。”
待她一切收拾妥当时,茵陈也已醒来洗漱好了在看着院里还干枯的花枝。
“郡主看起来好多了,”她见到薛容玦出来笑着上前扶着她。
茵陈扶着她坐在院内的石桌旁,今日天气晴朗,阳光慵懒随意地洒在她的身上,舒服又闲适,昭示着春日即将到来。
薛容玦看了眼茵陈刚才在瞧着的花枝笑着道:“茵陈也喜欢毛地黄吗?我这株是紫红色的,盛开时格外鲜艳,倒是我让人给你送些去。”
“那便多谢郡主了,”茵陈笑着道谢,又让小婢女拿来自己的药箱,拿出脉枕笑着看着薛容玦,“郡主可愿让我为郡主好好瞧瞧?”
薛容玦抬着自己的手腕放在脉枕上,笑着道:“那是自然。”
茵陈的手搭上她的皓腕,原本充满笑意的脸渐渐变得严肃。
“郡主可否让我看看舌苔?”
茵陈半晌后放下了把脉的手,斟酌着语言:“郡主的脉迟而无力,舌苔发青,此乃寒凝内阻所致。郡主可曾受过寒凉?”
薛容玦点了点头道:“去岁曾坠入荷塘,应是留下了些病根。”
月红急忙补充道:“何止呢,郡主当时昏迷了整整半月,初初醒来时神情恍惚,三四日之后才渐渐好转,只是自此后便格外怕冷,手脚总是冰凉。”
“果然如此,”茵陈点点头,“和我所料不差,可是除此之外,郡主近日可是常常失眠?”
月红惊讶地看着薛容玦,她在二人的目光下缓慢地点了点头:“入睡总是困难,每当入睡一点响动便会被惊醒,再入睡便格外艰难。”
茵陈又问道:“郡主可是有何忧心之事?”
薛容玦难得沉默,该让她怎么说呢?她每日都在为历史的走向忧心焦虑,心中总是不安,历史已然改变。
可是万事万物自有其因果,她改变了因又会带来怎样的果呢?
她从历史的看客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曾经的记载已经无法参考,每每念及此她便时时心慌到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