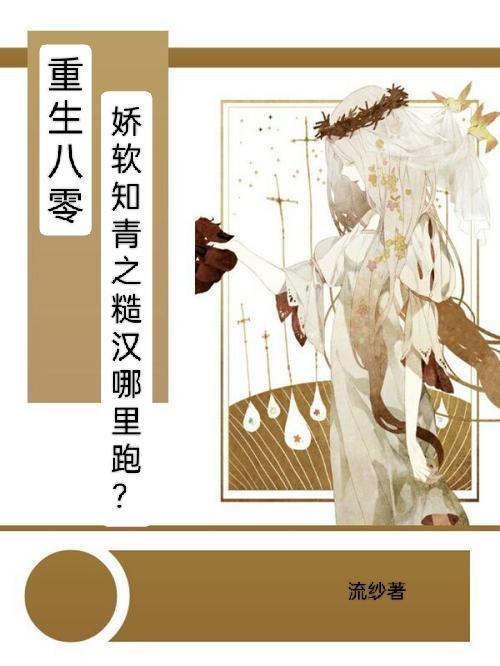凤阅居>我和姥爷的关系叫啥 > 第49章 广州站遭遇人贩子危情下救小姑娘(第1页)
第49章 广州站遭遇人贩子危情下救小姑娘(第1页)
小姨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大熊妈妈马上准备接九十多岁奶奶到家里,把几个小叔子担心的事全揽过来。说句心里话,大熊爸都没有这个胆识,大熊妈妈办事一点不含糊,说,“咱家条件好,又是老大,咱不办,谁办?提啥钱,别让弟弟们笑话。老婆婆的家底自己留着,心里有底,将来愿意给谁就给谁?”
四叔听说这件事,连竖大拇指,“服了,嫂子把咱们家老爷们该做的事都给做了。”三个小叔子一想,这也不能让嫂子扛啊,凑到一起,四叔出面,到大熊爸爸家。四叔说,“嫂子,见笑了,把咱们老爷们比的显小气啦。哥几个商量了,以后家里啥事都听你的,我们哥几个把赡养费交给你统管。”
大熊妈更有样,“老婆婆也是该我伺候的,钱不钱的,听你大哥的。妈能活几年,咱们条件比你们好,有钱没钱我都养。”
三姥爷一听说这事,就对小姨说,“你这个婆婆啊,还真的有点侠肝义胆,挺可交,回沈阳哪天我请她喝一杯。”我提醒三姥爷,“咱们可不能直老喝酒,毕竟是亲家母,能不能整点高雅的节目?”
三姥爷说,“有啥高雅的节目啊,咱们和人家体制内的能比吗?人家是吃皇粮的,咱们是走江湖的,只会喝酒。高雅的事根本不懂。”
我说,“哎,草根有草根的开心事,怎么不能有。咱们也可以请大熊妈妈去歌厅唱唱歌,也让她享受一下做老百姓的开心事。”
三姥爷说,“你那就是高雅的事啦?我看未必,咱们家就你最有文化,我倒是觉得老百姓就干点老百姓的事,有什么可装的。”
我说,“对,改天就请大熊妈妈去喝酒,说不定,一下子就放开了呢?”
大熊家的家务事顺利出关,三姥爷跟小姨说,“老丫头啊,落叶归根啊,广州这边拉也不好混,实在不行咱回沈阳吧,毕竟在咱们自己个的地头。”
小姨说,“大熊这边手术都排满啦,得挣点钱。沈阳那边不好整,广州多活分啊。另外这边有钱,有钱人就是惜命啊。”
我说,“小姨啊,你还差钱吗?三姥爷的那些家产不都是你的啊?”
小姨说,“你说错了,那可是我老爸拼死拼活自己个挣出来,我花那钱心里不踏实。自己就是有一分挣一分,挣不到的,我就和大熊喝西北风。”
三姥爷也没再接话茬唠,这个丫头啊和他自己个的脾气没有什么两样,一头倔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也无所谓,年轻人总的有点年轻人的气势出来啊。总之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情,总比成天没事打麻将强吧。
过了几天,三姥爷不爱在广州待了,就想着回沈阳,与小姨依依惜别,父女情深,也挡不住三姥爷回家的路。
广州火车站一如既往地脏乱差,尤其在出站口与广场二百来米的地段,简直是盖了帽的危险区,孩子能抱着绝不领着,包紧紧的护好,钱放在贴身的地方,行李箱死死地拉着,不要买任何的东西,不要打任何的公用电话,不要在任何摊位前驻足,遇见戴墨镜的绕开走,遇见三两成群又空手而来年轻人躲开,最最重要的是离摩托车远一些再远点。
我和三姥爷才不管那套哩,那天天气还特别地热,三姥爷把外面的小衫往下一脱,就穿个背心着。像三姥爷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对背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即使是穿衬衫,里面也得穿个背心。这种跨栏背心露出两个大胳膊,尤其是三姥爷的青龙白虎分外明显,隔着老远就挺吸引站岗的警察的注意,时不时过来查查身份证。
其实,穿这种跨栏背心是源于一种对于工厂的老感情。当年的劳模会上,一定有劳模身穿劳动模范的跨栏背心登台领奖,这更是一种殊荣。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即使是得了个茶杯子,那也会引起左邻右舍的羡慕和敬仰之情。
三姥爷说,“这广州啊,净扯这没用的,有那时间管管那些盲流子,穿的破衣啰嗦,多给广州人丢脸。”
我说,“可不咋地,比咱东北大兴安岭的小镇还差太远。不提了,你老要是抽烟的话咱俩得找个好地方,别让管事的给罚钱。”
三姥爷说,“不用这么样吧,那不有烟灰缸?”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的大烟灰缸子跟我说。
我说,“早就听说火车站专门有批人就是干这个骗钱的行当,咱们还是不惹事。”
出了广场,有个胡同子,我俩钻了进去。三姥爷蹲在一块大石头上点根烟,我则望望胡同子顶上狭窄的天空,两边高耸如云的摩天大厦,我更像那只从小镇走出来的井底之蛙,我心想这广州啥时候能高大上起来。
我忽然注意到,抽烟的大石头旁边有辆小微型车,太阳太大,正好乘凉。忽然在胡同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个小女孩,隔着车玻璃看到她正在问一男一女什么,好像是问路。问着问着,吵了起来。我正在玩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俄罗斯方块,小小的黑白屏幕从上面不断掉下来各种各样的条,或者拐把子,我按按钮再给它们摞一起。眼瞅着方块从上面往下掉,我也顾不上看别的,紧张得直按按钮。三姥爷夹着烟低声说,“怎么那个男的和女的,一个劲地要往车里拉小姑娘。”
我说,“人家是一家的,咱管那个闲事干哈?”
三姥爷说,“不对,那个小女孩一个劲地哭喊着。”
胡同很深,正是大中午,没有什么人,我们也躲在大石头后面,谁也看不到。三姥爷突然怼我一杵子,“不对劲,你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