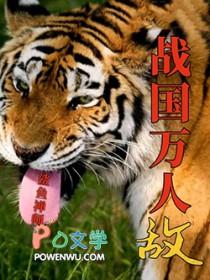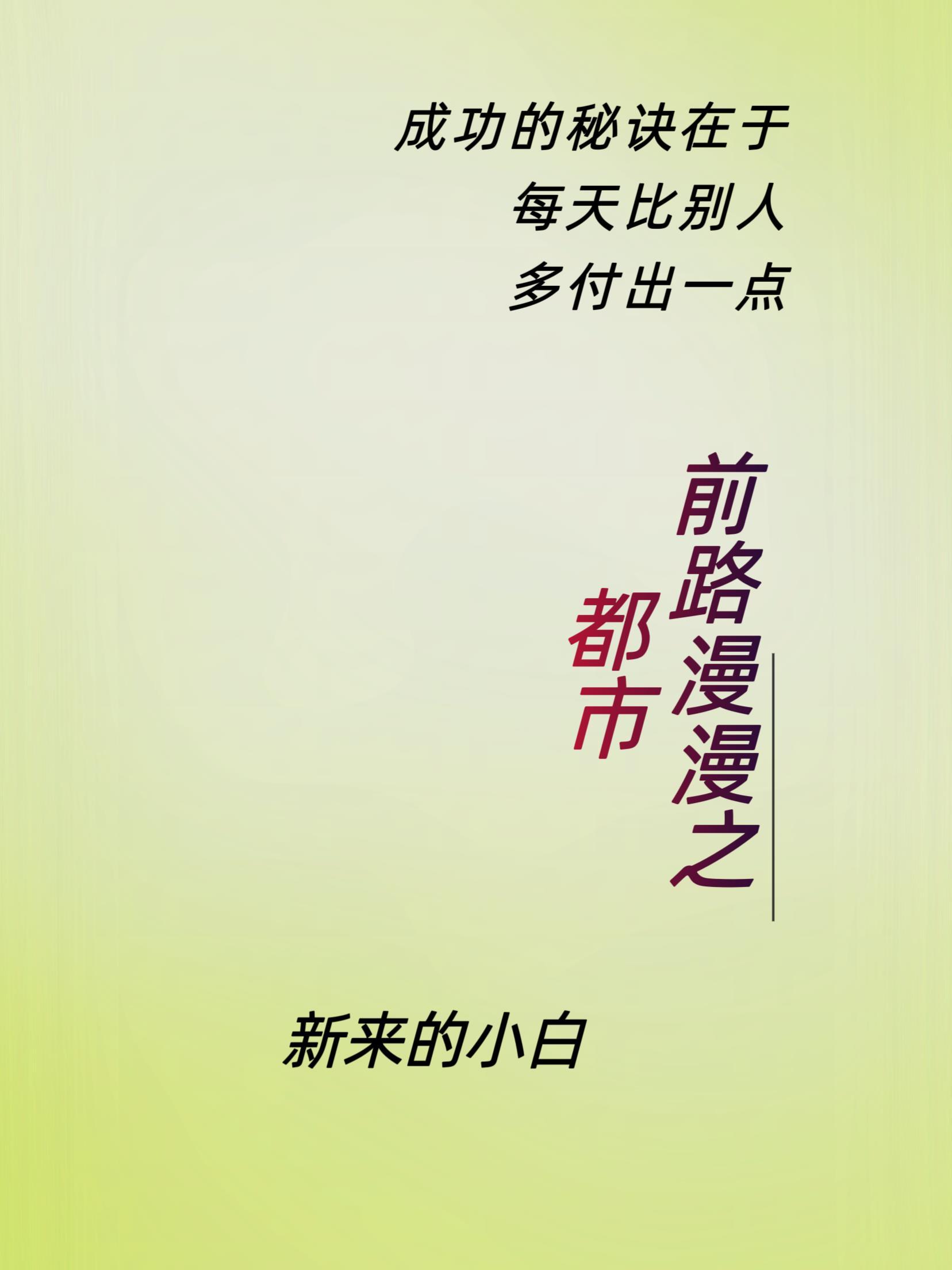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女神的斗士旧版本 > 第91章 娘家人(第2页)
第91章 娘家人(第2页)
有人说像海苔,有人说像山楂片,有人说有点甜,有人说有些苦,有人说好吃,有人说味道吃起来怪怪的。
这情景看得史寥龙傻眼,看得麦莹莹心痛。
“你们吃,这里还有,我闺女和女婿都会挣钱,我女婿上个月挣了三十万。”
丈母娘说着把盒子里剩余的阿胶片下,就像幼儿园的老师给孩子们糖一样。街坊们一听一个月就挣三十万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史寥龙。
乡亲们的目光那叫一个纯朴,那叫一个羡慕,那叫一个隐隐的妒忌与不甘心。还有人叨咕道:一个月挣三十万,一年就挣了三百六十万!
这些上了年纪的村里人,心里除了羡慕,也都在怨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像麦家的这个女婿一样有本事,自己的女儿为什么当初没擦亮双眼找个像麦家这样会挣钱的女婿。
虽然这里不是史寥龙的家,但史寥龙被一群人这样盯着瞧还真有些不适应,好像他是个成功人士这次荣归故里!
“史寥龙,你挣这么多,干脆把家里房子重新整整,修个三层楼高的楼房啦。”
有人随口说了这么一句,史寥龙抠着脑袋笑了笑,说没大家想的那么多。
他进到老家的房子里,现到处堆的是东西,吃的、喝的、用的、摆的、穿的,乱堆乱放,堂屋和几个房里杂乱无章。
这哪是要办喜事的样子,光秃的墙面连个婚纱照都看不到。他想这喜酒看来是办得急,怕新媳妇的肚子大起来街坊讲闲话。
麦红和朱莎莎只到晚上八点多才回来。麦红说幸好赶上了镇上最后一班巴士,不然今天回不了村里。
即将成为新娘子的朱莎莎却没有一点亲娘子的喜庆样,反而板着脸,见了麦莹莹与史寥龙也只是应付地点个头,打声招呼。丈母娘问她吃过晚饭没,家里还有排骨汤,要不给她热一碗。
朱莎莎却甩脸色给丈母娘看,一声不吭,从抽烟的老丈人面前走过时权当空气,开门进房之时又扭头好像对着屋子里所有的人说:
“家里有孕妇还抽烟,有没有文化,有没有一点常识!要是以后孩子生下来有问题这个责任谁承担?”
说罢,人进房,房门关起时啪地一声响,几乎把墙上的粉尘都给震下来了。
老丈人继续悠闲地抽烟,好像听不到也看不见。丈母娘见怪不怪地问麦红自家媳妇早上出门好端端的,怎么又开始起神经了?
麦红的眼睛注意到老丈人桌子上摆的烟,像是现新大6地:“哇,1916,这烟猛呀,抽根试试。”
说着连忙掏一根出来用打火机点着。丈母娘上前拦住,怨儿子怎么还抽上烟了,抽烟费钱,这都要结婚了,以后孩子生下来还有好多地方要花钱。
麦红一喷烟雾,像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地:“老爸,你财了,是不是看我明天结婚你拿私房钱去买这烟撑门面?”
老丈人呵呵一笑,说:“这是你哥买来的。”
麦红吮着烟一看史寥龙,压根不信地:“我哥买的,我哥还不是拿着我姐的钱来孝敬您老,反正都是一家人,谁花谁的钱无所谓是吧。”
史寥龙懒得搭理,掏出手机耍。
麦莹莹一直瞅着紧关的房门,最后也忍不住问:“麦红,这朱莎莎是怎么了,跟个火药罐似的,你们在外面吵架了?”
麦红说:“今天去市里照婚纱照,拍的是内景,我看效果还可以,所以外景就取消了。再说那个小县城又没啥风景区,到处跑不仅人累还折腾钱,所以朱莎莎不高兴了。”
丈母娘觉得不对劲地:“昨天晚上不是听你们商量好了,不拍外景,朱莎莎是答应了的,怎么今天又为这事闹脾气?”
麦红白了老妈子一眼,怪老妈子拆穿自己,又说:“婚纱照是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是饰的问题。我们昨天也是商量好的,项链加戒子预算控制在八千以内,她倒好,今天在珠宝店被人家销售洗脑了,追求更高级别的,算下来得一万六。我说她胸大无脑,听别人忽悠,她就跟我耍性子,脾气。”
这话一听丈母娘立即和儿子站同一阵线了,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意思是儿子做得对,这媳妇还没正式过门就开始漫天要价了,以后由着她性子来那还得了。
老丈人喷着烟子地说了公道话:“也不完全怪人家朱莎莎,女人嫁人一辈子也就一次,她肚子还有娃,她生气就会动胎气。”
丈母娘不乐意了,叉腰质问自家男人地:“你说得好听,她肚子有娃就要惯着她,我以前怀老大生老二你有哪次听我的了,给我啥子了?现在你大方,你想做好人,你拿钱出来给她买饰?咱们家什么情况她又不是不知道!”
老丈人把头冲儿子那边一摆地:“红你拿钱出来,你也上了几年班,还是当领导的,这点钱应该有。”
麦红一听立马有些怂了,随后讨好地笑道:“钱嘛我是有的,但不能乱花,饰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吧。我这钱是留给我孩子出生用的,什么医院呀,主刀医师呀、娃的尿不湿和奶粉我都是通过以前的同事打好关系了,用的都是最好的,拿的都是内部价!”
史寥龙有意拆台地:“你不是辞职了么?”
麦红朝他挤眉弄眼地:“我的下属个个服我,想让他们办点事太简单了,就一个电话而已。我人走了,但威信还摆在那里!”
史寥龙借力打力地:“噢,是能力上的威信还是手机里的微信?”
麦红气得把烟头扔地上用脚捻。
俩老是听不出儿子和女婿对话中的含沙射影,反而被麦红完全洗脑了。俩老认为儿子这话讲得有道理,儿子有钱不能乱花,钱是结婚过日子的,钱要用在刀刃上。
房门突然打开了,朱莎莎大步流星地走出来,看样子外面人的谈话这未过门的媳妇是全都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