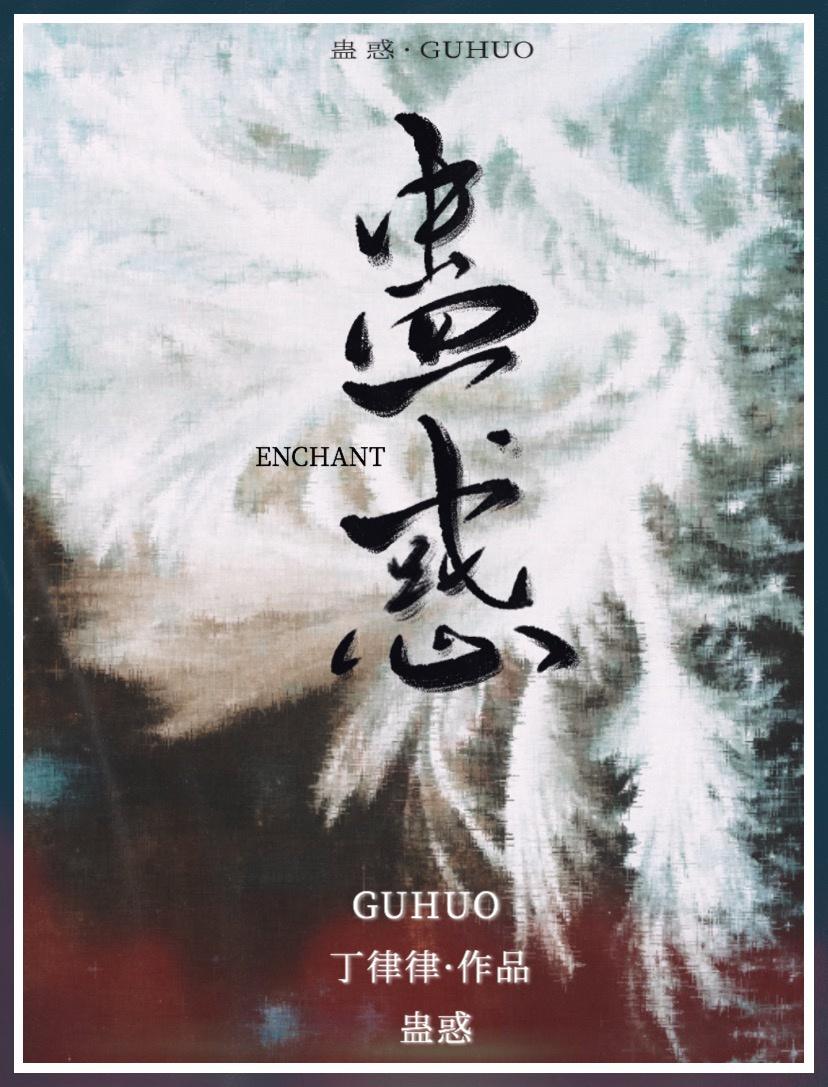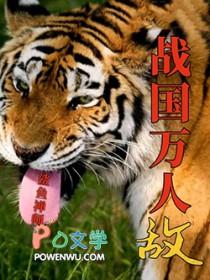凤阅居>美女扶栏杆背影照片 > 第84章 罗敷有夫(第2页)
第84章 罗敷有夫(第2页)
云乐舒爱不释手,拿在手上便忍不住试了起来。
几声悠扬的曲笛自白玉笛而出,摊贩便如王婆卖瓜,不停地夸赞道,“这白玉笛声音清透,不同凡响,别人家的玉笛断没有这一把吹得出色,姑娘您真是好眼力啊。”
云乐舒抚摸着笛身轻轻一笑,“确实不错。”
却不知身旁什么时候多了个男子,趁她不注意快手夺走她的笛子,举在头顶,转头与摊位老板道,“这位姑娘出了多少钱买下的?我愿出双倍。”
老板面上露出为难的笑,“公子,凡事有先来后到,方才这位姑娘已付了钱,您要不看看余下这几支有没有合眼缘的?”
“我只看得上这支!我就要这支。”那男子虽面朝老板,眼睛却不时往云乐舒身上瞟,语气虽说很无赖,面上却笑吟吟的,略带几分猥鄙。
老板客气地指了指云乐舒,“那公子便只能与这位姑娘私下相商,看她是否愿意转卖了。”
那男子不怀好意地透过纱帘打量她,轻狂无状,语带威胁,“姑娘,不如这样,你揭开帷帽,我便还你玉笛。”
云乐舒哪里肯,眼见周围已有三两爱看热闹的围观过来,只想快些脱身,便轻踮脚尖,一把将玉笛攫夺回来,淡漠转身欲走。
那人却抓住她的玉臂,不肯放她离开。
老板看得着急,却也无能为力,只暗暗骂那人无耻。
是不是金陵盛产色鬼,怎么她戴着帷帽也有人来调戏啊,云乐舒也在心里骂。
见这边动静闹得越来越大,她只好硬着头皮回身,换了副笑脸,“公子,若你真爱此物,此物赠与公子也是可以的,只是我家夫君管得严,心眼小,又是个粗莽之流。。。。。。他若是知道我当街与一男子拉扯,公子你可禁不起他一顿混打,粗人听不得细话,他可不会听我解释,便只有拳头是最解气的。”
那男子一听罗敷有夫,相公又好像是个不好惹的,便也息了心火,扫兴地放开她的手。
“夫人,等你半天都不来,在这里做什么?”岳暻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将她护在怀里,往那男子面上略略一瞥。
那男子只觉得冷飕飕的,身上莫名生出一阵寒意来。
当街调戏人家的宠妻,人家万一真的把他暴打一顿,他岂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那男子忙嬉笑哈腰,“方才与令夫人有些误会,已经解开了,若无其他事,在下先走了,呵呵呵呵。”
岳暻面露不悦,看着他那只碰过云乐舒的手,显出一丝狠戾,随后与流川使了个眼色,又微微摇了摇头,才转头打趣地问她,“为夫管你管得严?心眼小?粗莽?”
云乐舒没想到他会出现,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您自然是宽容体贴,心胸广袤,文质彬彬,方才不过随口敲打敲打他罢了。”
“算了,不与你计较,回去吧,省得你再给我惹出事儿来。”说罢便拨开还在看热闹的路人,牵着她的手离开。
“那位相公相貌出众,风度翩翩,怎么被那小娘子说得像个乡野村夫?”有人笑道。
“瞧他们二位,应是新婚燕尔吧,还牵了手呢,我瞧着这便是夫妻情趣,你不懂吧?”
“不过那公子倒生得一副富贵名流之相,小娘子虽头戴帷帽,应该也生得不错,如此才算得上珠联璧合。。。。。。”
“也难怪会遭人当街调戏。。。。。。”
“生得再好那也不能这样轻浮浪荡啊,若是遇到个不经事的小娘子,那不得把人吓坏了?”
“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两人快回到渡口时,云乐舒才想起流川来,忙问道,“你那位手下呢?”
“我让他去办件事。”岳暻仍牵着她的手,淡淡道。
云乐舒哦了一声,想起方才那男子想摘她帷帽的举止,还有围在她身旁的看客,仍觉得心有余悸,本来还想再四处逛逛的,现在却只想回到船上,生怕引出枝节来。
荷风拂面,她从岳暻手中抽出手,将鬓边的散顺了顺,信步上了船。
不一会儿,薛娘子和流川一前一后回到船上。
流川向岳暻、云乐舒行了礼,又不着痕迹地朝岳暻点了点头,才把云乐舒的书和衣服饰送去房间。
薛娘子命守卫把大几篮子食材用具放到杂物房,转头与云乐舒说道,“姑娘方才可听说了?有人在暗巷遭人凌殴,生生打断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呢,据说那人下手极狠,关节处的骨头皆被伤得粉碎,只怕今后便是个废人了。”
船老大听到薛娘子的声音攀出头来,见人都回来了,便起了船,听到她说什么有人被打断手脚,只不以为然地笑笑然后回了船舱,跟着王上这些年,什么血腥场面未见过,断手断脚算是什么了不得的。
云乐舒惊诧道,“啊?还有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