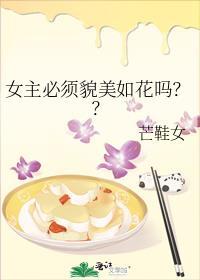凤阅居>三七助学和五五助学 > 第5章 五国公约(第1页)
第5章 五国公约(第1页)
“这三局两胜,乃是双方对阵三局,赢下两场则为胜出。”见王爷问起,李国发连忙答道。
“啊,竟有如此说法?”王爷诧道,“两军对战,难不成胜负尽押三人身上?”
“却是合该如此。”李国发拱手回道,“我大周乃是天下正统,自当谨遵五国公约,南越既下文斗战书,断无不应之理!”
“五国公约?”
戴丁勇见王爷仍是不解,立时便明白过来。
想是先帝在时,过于溺爱这三皇子,平日里承欢膝下,却是不曾对其讲解战场之事,也是存了让他远离杀伐之意。
只是身为大周王爷,若是对这天下大势不甚了了,倘将来时局有变,却是大周灭顶之灾。遂上前一步,长声说道:
“王爷有所不知,数百年前,这天下却并非现在之格局。彼时四分五裂,竟是有大小国上百余。一时间,争乱不休,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无心耕种,盖因性命朝不保夕,大多有种无收,倒不如扛了刀枪,也上战场厮杀一番,或有生机。一时间,虽人口萧条,却是兵多粮少。”
见王爷果然大感兴趣,便接着说道:
“眼见这天下血雨腥风,即将分崩离析,横空出世一道人,自昆仑山而下。这道人,游走各国之间,最后选了五个实力大国,邀其君主赴昆仑共议。想是五国君主亦是明白,长此下去,实是天下苍生之大不幸,竟是皆同意了赴这昆仑之约。一时间,消息传出,各国君主倒是十有八九自发前往,齐上了这昆仑山顶。”
王爷听罢,一时心驰神往,赞道,“这昆仑道长,实是有大格调!”
戴总兵微微一笑,接着说道:
“往后这昆仑共议,却是每年皆会举办一次。各国广发言论,旨在休养民生、减少杀戮,最终以五国共同认可为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套规矩,包括不杀平民、不屠战俘,乃至文斗之法,均记录在案,再以五国君主共盖国印为准,史称五国公约。”
王爷这才明白,颔首道,“原来这便是五国公约。”
“而后,诸多小国为求安稳,纷纷在这五国之中,自选其一,称藩国、行岁贡,依附其中。此举,亦需借由这昆仑共议之机,向天下宣称方始生效。如此,这中原大陆,终于尽归五国。”
“这昆仑共议,实是造福天下苍生之举!”王爷赞不绝口,问道,“想这五国,自是有我中周,另三国乃是南越、西凉、东璃月,却不知这北境之外是哪国?竟是需耗巨资、驻死军以抗之,先皇在时,曾明令天下:遵祖训,北境之兵,国亡亦不可回防。众臣工均是不解,皇亲亦纷纷上书劝谏,先皇却是厉声呵斥,只说这收回旨意,是万万不能。”
“却是不然。”戴总兵抚须笑道,“我大周自是这五国之一,南越、西凉却也不错,只是现今东岛这璃月国,却是不在之列。相传,当时天下纷争之际,有一股中立势力,号璃月神教,游走各国之中,广收信徒却不涉战争,只是一味地出海探寻,终是寻到了去处,遂令教众造船数百,举教迁之。彼时,各国自顾不暇,倒是无人问津。此后,这璃月神教便沓无音讯。直到百余年前,才有璃月使者返还大陆,朝廷遂也派人出使。大皇子,现今的镇北王,便随使者去过这东岛璃月。”
“此事我却是知晓的。”王爷抬首说道,“大哥从璃月归来,向父皇言说,璃月国不兴刀兵,举国上下,竟是财产无私,用之则取。父皇却是不信,言道,便是亲兄弟,尚需把账算在明处,焉能公产自取,岂不乱套?我当时正好在旁,听后也甚觉奇怪,难不成这璃月之人,竟是全无私心?”
“王爷若是感兴趣,回京后大可请示皇上,去璃月一探究竟。”戴丁勇接着说道,“这北境之地,千余年来,皆是只进不出,北境之外,到底是何方势力,却是无从知晓。”
“既无人知晓这北境到底战事如何,那这军饷、兵源,年复一年地往北境输送,是何道理?”王爷又问。
“此事到底是何缘由,却是只有皇帝一人知晓。大周每有新帝即位,须前往太庙,于先祖神位前立下誓言,先行承诺永续北境战力,方可荣登大宝。”戴总兵说完,见王爷似又要发问,便接着笑道,“王爷怕是要问,仅凭这一条祖训,却是如何延续至今?毕竟这北境消耗,实是巨大。”
“确是有此疑问。”
“皇家祖训尚有一条,君临三载期满,皇帝可于太庙,请夏国旧印,赴北境劳军。历代君王,自北境返京后,却是绝口不提该处所见,只言这北境军资,定要如期送到!”
“夏国旧印?”王爷连忙问道,“这夏国也是五国之一?”
“不错。”戴总兵接道,“彼时夏国,军力雄厚,实是五国之首。反而我中周,在五国之中实力却是最弱,虽与夏毗邻,倒未受其欺,反是受益颇多。然凉国却不甘人后,伙同燕国,举兵共伐大夏。”
“这燕国,便是这五国之中的最后一国了?”
“正是。”戴总兵接着说道,“这大夏也是当真了得,以一敌二竟是未落下风。凉、燕见久攻不下,便派使者游说我中周和南越,言这大夏实力过于强大,若不围而灭之,则四国必然难保长久。南越终是被凉国说动,起兵加入讨夏联军,我中周自是不会恩将仇报,对夏国倒戈相向,却也不便与大夏结盟,只是暗地里输送些战备物资,以尽国谊。”
“实是欺人太甚!”王爷接道,“彼时若是大哥已出生,便是我大周不肯出兵,他也定要孤身前往,以助夏国。”
“想是当时国力确有不堪。”戴总兵说道,“为君者,自是以本国百姓为重,却不可逞血气之勇。”
“以戴总兵之见,我大哥便是徒有匹夫之勇,故与大位失之交臂?”王爷怒道。
“属下并无此意。”戴总兵见王爷动怒,却已然不惧,显是已看出这王爷实是并无城府,喜怒形于色,却是真性情,倒是容易相与。
“镇北王乃是我大周之脊柱,便是当今圣上,也自称不及项背,属下岂敢轻视!”
王爷听罢,微微颔首,接着叹道,“想必那大夏,以一敌三,虽有我大周供些物资,怕是也无力回天。”
“原该如此。”想是讲述久了,有些舌干,戴丁勇咽了咽口水,润了下嗓,接着说道:
“只是那南越国国君,亲率了三军,抵达战场后,却是一兵未出,便原路折返了回去。”
“这是何故?”王爷大感惊讶,接着问道:
“莫不是那南越,尽是些绣花枕头,只会些个三局两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