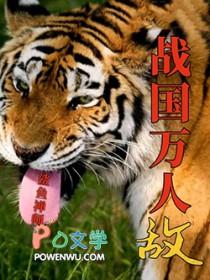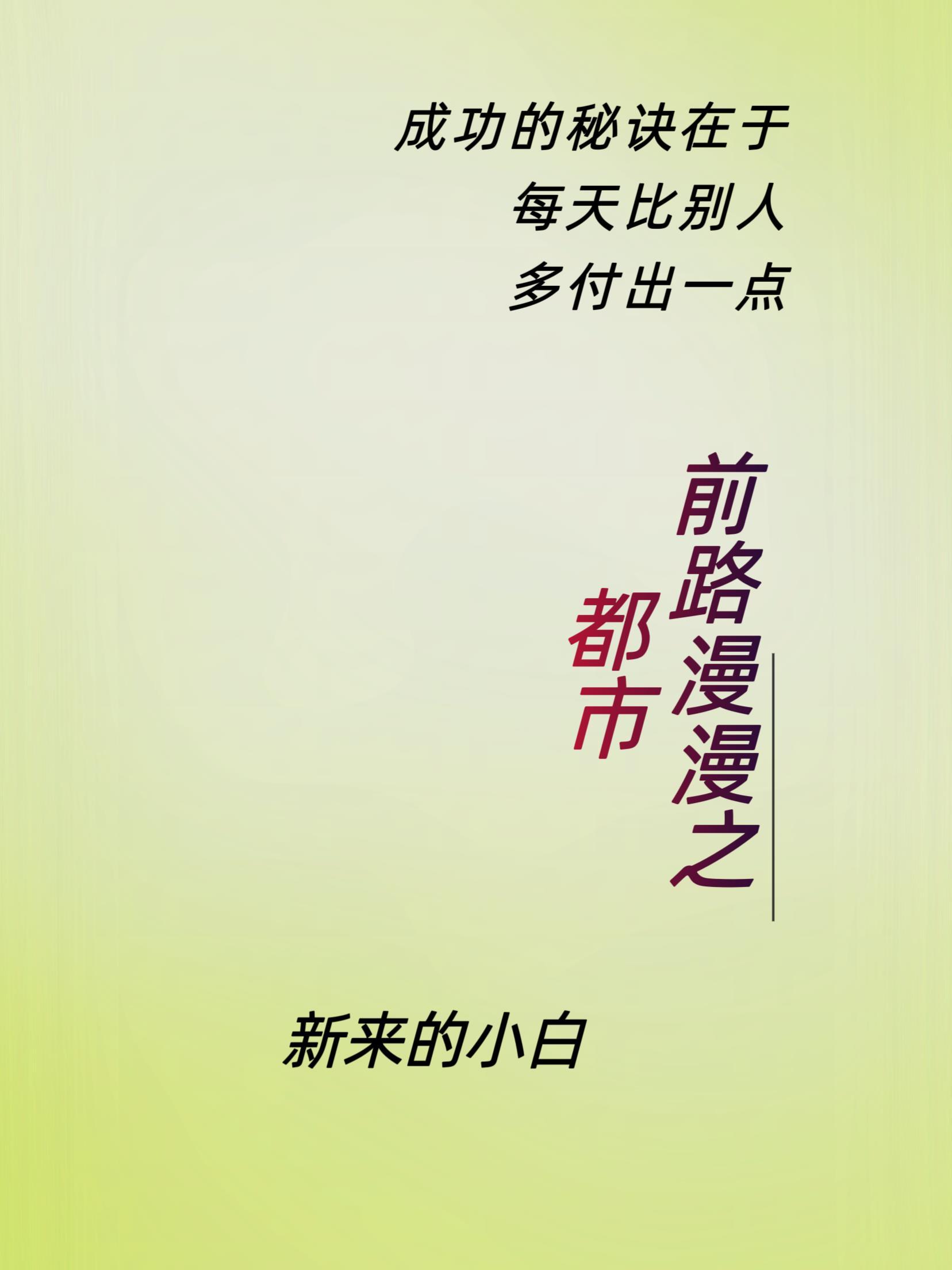凤阅居>试谋未遂边棠资源 > 第21頁(第1页)
第21頁(第1页)
沈渡津側頭看了眼盛閔行,此時他別無他法,他扮演的角色是盛閔行的「人」,自然一切都聽盛閔行的。如果時間倒流能再給予他一次選擇的機會,他更寧願被復縉痛快地扇一巴掌或打一頓解氣。
他實在不明白幾分鐘前自己到底抽的什麼風,竟然相信盛閔行所說的解圍是真心實意的要幫他,他剛才甚至還生出了一瞬間「盛閔行人還不錯」的想法。
盛閔行一個月以來從沒做過出格的事情,這或許就是他對盛閔行放低戒備的原因,這就像慢性毒藥一樣,經久地滲透,麻痹他的神經。
他似乎有些淡忘了盛閔行的最終目的是什麼。
真是愚蠢至極。
盛閔行臉上掛著意味不明的笑,用眼神示意他喝。
他用力閉了閉眼,鬆開因咬合過緊而發酸的後槽牙,縱使有再多不情願也乖順地捏起那隻酒杯。
沒有過多言語,他也不懂如何品嘗這種昂貴的酒,頭一仰酒杯一抬,冰涼微澀的酒液順著喉間流淌而下,一直下落到胃底,碳酸受熱分解產生的氣泡刺激胃壁,激得沈渡津皮膚上起了一層小顆粒。
多少讓人有些不適。
復縉見狀笑道:「盛閔行沒教過你嗎,香檳不能這么喝,要小口慢酌,緩慢品咽。」
這種無異於指著鼻子說「沒見識」的行為多少讓沈渡津感到赧然。但他只能緊攥著酒杯任由復縉取笑。
復縉罵的不僅是沈渡津,還有盛閔行。他意有所指,盛閔行不會管教情人。
盛閔行也說不清是為自己爭口氣還是單純因為沈渡津被取笑,他接過沈渡津手上的杯子重倒入小半杯酒後送回到他手上,再次摟住沈渡津,溫聲道:「我教你。」
指尖交觸之間,沈渡津胃裡的不適更加明顯地放大,仿佛與盛閔行搭在他腰上的那隻手連為一體,讓他反胃。
他的手被盛閔行握著,手心是冰涼的杯壁,手背是盛閔行的體溫。他有些抵抗這樣的觸碰,最終卻抵不過盛閔行施加給他的力量,杯沿再次碰上唇瓣,抵住貝齒。果香與酒氣在舌尖縈繞,容易讓人沉淪於醉生夢死中。
這是夜場第一名酒的味道,可沈渡津一點都不喜歡。
小半杯酒硬是被盛閔行分成三次送到沈渡津口中,當最後一滴酒離開杯沿時,沈渡津終於忍不住了。他不願意再陪盛閔行演下去,幫他解圍只是空虛的漂亮話,盛閔行真正想做的並不止這麼簡單。
於是他將手背到身後,在暗處撤下盛閔行的手,並有意識地往旁邊挪了挪。
盛閔行也覺得夠了,沈渡津不是個好惹的,他必須得收著勁,逐步攻略。再者,甜頭不能一次嘗得太足,否則容易喪失後面的樂。
他順勢放開手,呈大字型仰靠在沙發上。
復縉沒打算輕易放過沈渡津,盛閔行放了手,他便再次發難。反正這個包間裡除了盛閔行沒人會看重沈渡津,畢竟也只是一個玩物而已。
沈渡津正襟危坐,與不遠處那些橫七豎八的光景格格不入。
復縉重給他續上酒,開口道:「鍾期跟你說什麼了?」
「什麼都沒說。」沈渡津無視那杯淡黃色的液體,垂下眼帘盯著自己的鞋尖。
「不用不承認,他肯定跟你說過不少。但他肯定沒挑重要的說,我想說點沒刪減過的。」復縉手裡的酒杯早已變空,他舉起杯底對著光看了一眼,隨即放回原位。
沈渡津低著頭,看起來像是在極力忍耐些什麼。盛閔行覺得有,這副表情著實鮮,他能觀賞很久。
復縉也不理他,自顧自地說道:「從哪裡說起呢?從他偷偷爬我netg開始,還是從他跪在地上求我包他講起?」
……
復縉每說一句,沈渡津就噁心一分,漸漸地復縉在他眼裡只有嘴在動,說的內容他選擇性的屏蔽掉不少,但還是有部分漏進了他耳朵里。
他臉色極差,冷冷道:「別說了。」
任誰都不想從別人的嘴裡聽見友人的不堪,更何況說這些話的人和鍾期曾經是那種關係。
「當然可以,」復縉露出個陰惻惻的笑,「你喝一杯,我就少說一句。」
「復先生考慮好了?」沈渡津當然不願意,自我貶低道,「我這樣的人似乎不配多喝這麼貴的酒。」
復縉十分大方:「喝吧,總歸你可能只有這一次機會。」
沈渡津咬咬舌尖,試圖從被羞辱的痛苦中清醒過來,「這其實並不公平,您說多少句話由您自己決定,我喝多少杯……根本上還是由您決定。」
「公平?」復縉像是聽到了什麼了不得的東西,故作驚訝,「那這樣吧,你喝五杯,我一句都不多說,怎麼樣?」
沈渡津皺皺眉,快地掃視一眼盛閔行,盛閔行好整以暇地看著他,並沒有任何出手援助的意思。
也對,剛才是他先厭棄在先,是他「給臉不要臉」,盛閔行翻臉不認人也無可厚非。
他重正視面前這杯酒,清瑩透亮的酒液上漂浮著些許泡沫,在燈光下反射著異樣的光彩。
一杯。
兩杯。
喝到第三杯的時候,他透過杯底看了一眼對面復縉的表情。他這幾杯喝得遠比最開始時更凶更猛,可復縉什麼也沒說,這更加驗證了剛才是在故意挑刺。
一切都是故意為之,可他逃不掉,只能被迫接受。夜幸向來視顧客為上帝的上帝,從來不會有人為他這樣的人主持公道。鍾期被擠壓下去就已經是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