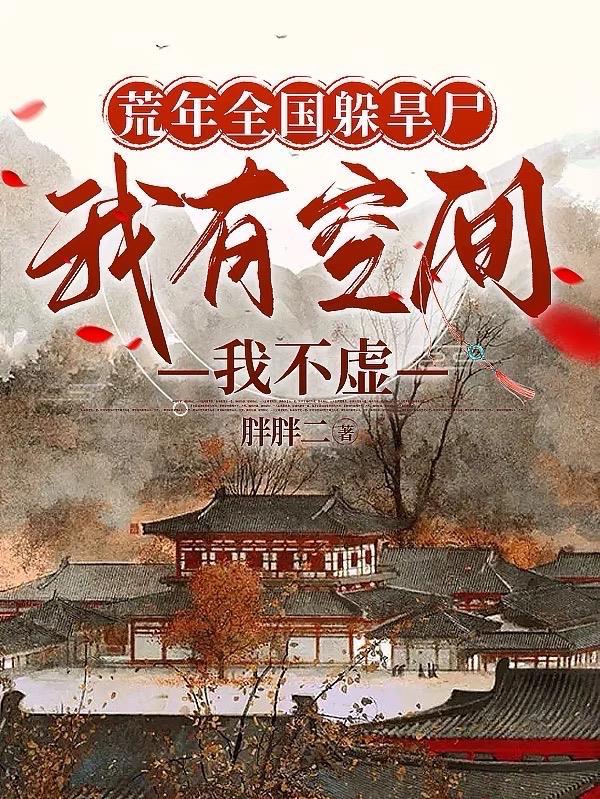凤阅居>锁南枝原文 > 第33章 长夜(第1页)
第33章 长夜(第1页)
下人们被吓得尖叫得四散奔逃,胆小的直接吓昏了过去,严氏哀嚎一声,立刻冲过去抱住陈维岳的腿,将他往上托举,大骂道:“快来人,快来人,救人。”
陈安年也奔过去,抱住他的腿,嘴里不断地叫道:“岳儿,岳儿…”。
下人们才缓过神来,立刻有人过去一起托举着人,还有人去搬了梯子,才剪断了绳子,将人放下下来。而陈维岳已两人翻白,气若游丝。
众人乱作一团,谁也没有注意到,凌乱的牌位中,多了一个。
下人合力将陈维岳抬了回去,此时府里的郎中也正好到。
严氏与陈安年立刻退到一边,郎中细细地检查了一番,面色沉重地摇摇头,道:“老夫可施针用药,帮助三公子早日苏醒,可三公子窒息世间太久了,伤了神志,即便是醒过来,只怕会成了痴儿。”
陈安年闻言腿软的一时站不稳,往后退了两步,下人眼疾手快的将人扶住,严氏则呆愣了片刻,奔道床边,搂住陈维岳失声痛哭起来。
过了许久,严氏哭得嗓子都哑了,不肯死心地命人再去请大夫,连宫里的御医也都请来了,一次次的检查,得到的都只是同一个答案,一直闹到后半夜,陈安年体力不支,在下人的劝解下,回房休息了,只留严氏陪着陈维岳。
房间里烛火通明,陈维岳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始终没有醒来,严氏双眼肿胀,哭得通红。此时轮椅转动之声响起,严氏抬眼望去,便看见元阳推着陈钰川来到门口。
严氏目露凶光,突然站了起来,直奔门口而来,话不多说,抬手就是一巴掌,元阳反应极快,闪身上前,脸上立刻印上一个清晰的手印,瞬间肿了起来。
严氏见此暴怒,大骂道:“好一个忠心护主的好狗!既如此,我成全你,来人,将这个贱奴拖下去,乱棍打死!”
下人刚要上前,陈钰川抬眼撇过去,那眼里的阴狠叫人心下一颤,都愣在了原地,畏畏缩缩地不敢上前。
“母亲这是何意,即便是尚书府,也断断没有将人随意杖杀的权利,这要是传出去了,父亲大人恐怕乌纱难保啊。”陈钰川看着她,眼底有不达眼底的笑意。
“是你!一定是你!”严氏恨得咬牙:“是你害了岳儿,是你!”
“母亲这话从何说起呢?我被困于轮椅之上,元阳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下人,府里的祠堂,日日夜夜有人巡逻看守,我们要如何将三弟吊在一丈高的房梁之上呢?
许是父亲官场上位高权重,惹人眼红,被人报复了吧。又或许三弟在花楼里招惹了权贵,也说不定啊。”陈钰川不急不缓地说道。
即便是恨得牙痒痒,可严氏没有确凿的证据,陈安年近年来官场上越来越依靠陈钰川出谋献策,若是想要一击毙命,她必须手里有铁证。
暂时压下心中的惊疑,她咬牙道:“胡说八道,晦气的东西,滚回你的玉笙院,若让我查到了岳儿一事与你有关,我定扒了你的皮!”
对于她的威胁陈钰川丝毫不放在心上,微微伸着脖子往床上看了一眼,惋惜道:“母亲节哀,三弟纵然痴傻,陈府也养得起他,只是…”。
“只是什么?”严氏怒目而视。
“只是一个痴傻嫡子的名号,传出去不太好听,不知道于父亲官场来往有没有影响呢。”陈钰川颇为遗憾地说道。
严氏被气得几乎失了理智,瞪着双眼想要吃人一般:“当年的那一碗红花没有杀了你,倒叫你成了一个面目丑陋的残废,像你这种浑身恶臭的东西,就不应该活着,当年真该和那小贱人一同死了才好!”
陈钰川闻言嘴角的笑意,慢慢落了下来,眼底阴沉一片,紧紧地盯住严氏。严氏自觉口不择言,可此时此景,她也顾不得许多了,转身回到床边,头也不抬地道:“滚出去!”
陈钰川静了片刻,点点头,自说自话缓缓道:“是该一同死了才好。”严氏没听出他话里的深意,就见他推了轮椅出去了。
还没走两步,就看到了窗下站着的去而复返的陈安年,两人相遇,四目相望,皆是一愣,陈钰川不欲多说,直径走了过去,又似乎是不甘心似地停下来,问了一句:“当年的事,父亲可知道?”
陈安年背对他,连头都不敢回,结结巴巴道:“我…我…我也是后来才…”。
陈安年有些自嘲笑自己多此一问,他没在停留,离去了。
两日后傍晚,陈府大门被人急扣,门一打开,竟是二公子陈旭然与管家于征。听闻严氏病重,陈旭然便快马加鞭赶回来,人一路风尘仆仆地走到了厅中,边走边问:“母亲呢?病瞧的如何了?大夫怎么说?”
下人被劈头盖脸地一问,都蒙了,陈府出事的是三公子,为何二公子只问夫人?只好道:“夫人无事,二公子稍歇,小人这就去请。”安顿好了人,然后着急忙慌地赶紧去后院请夫人去了。
下人的话叫陈旭然稍安,却又疑惑,回身看着身后的于征,后者眼神闪躲,不敢和他对视。陈旭然正欲开口询问,一道声音便传来。
“怎么不给二弟看茶?”陈旭然看过去,却是一愣,陈钰川久住玉笙院,他们好些年没见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