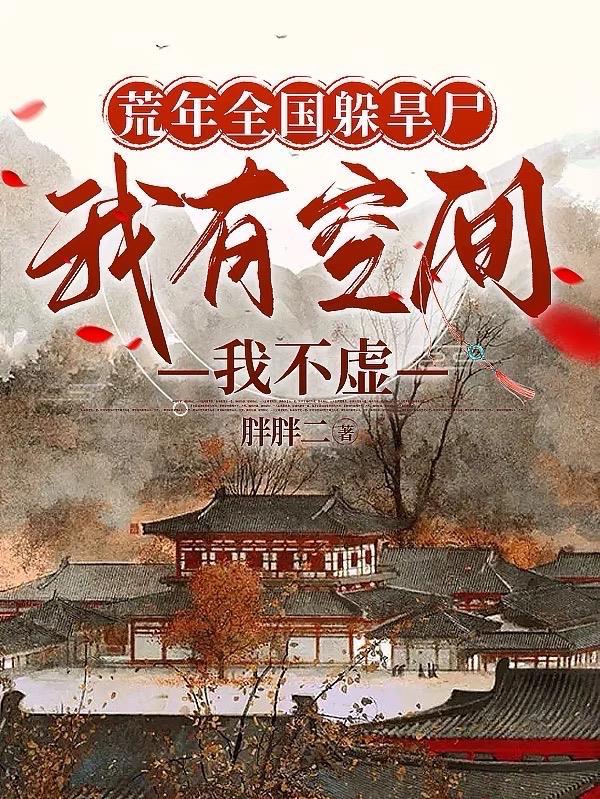凤阅居>短暂暧昧过 思念对方他会感觉到吗 > 分卷阅读70(第1页)
分卷阅读70(第1页)
了顿,回头扫了扫楼准,同样是那双漂亮的眼睛,但楼准感觉这道视线好像有些不一样。
淡淡的,像是平日里看习惯了,甚至给了楼准有些漠视的错觉。
“今天你要进来?”声音也没什么情绪,楼准似乎听出了几分嘲弄。
他小幅度地点点头。
那人松开了勾着门的手,静静地看着楼准走进来,门被关上,出不大不小的“砰”的一声。
同时出响声的,还有楼准微微疼的脊背。
他被薄朝推到了刚刚关上的门板上。
薄朝凑上前,一改刚刚冷淡的模样,勾着唇轻轻蹭了蹭楼准的喉结,离开时像小猫一样咬了一口,让楼准不可避免地滚动喉头闷哼一声。
他餍足地笑了笑,没出声音,只是两人贴得太近,小幅度地动也被察觉地一清二楚。
薄朝已经习惯这间屋子里楼准的存在了,特别是晚上,白天和他毫无关联的人几乎都会按时出现的,从最开始的美梦,到现在已经几乎成了梦魇。
在这间屋子里,楼准每时每刻都在他身旁,任凭他做些什么,但梦是梦,梦里的人没有现实的灵动,更提不上和现实中一样回应他,梦里的人只会像木偶一样,呆板地任他做些什么。
偶尔他也会做些两人不待在这间屋子里的梦,但梦里的楼准不会进来,像是游戏人物有着出生地,外界和屋内被割裂成两个世界,梦永远不连贯。
但这次,“梦”里的楼准进来了,这让他觉得有些奇怪。
薄朝没多想,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他是梦的主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忽略楼准垂下的灼热眼眸,往后退了两步靠在进门台上,抬手摘掉了楼准戴着的眼镜,随意地丢在了台子上,和玻璃碰上出响声。
“你为什么要戴?这明明是我的。”他喃喃地有些埋怨道,像是本来就不期望能得到回应。
“你戴着很好看,我想试试。”梦里木讷的木偶突然开了口。
薄朝一怔,半晌后缓过来:“不要戴,会挡到它。”
“谁?”
两人又静下来,屋内的灯没躲开,只有阳台落进来的月光,薄朝就着月光移动着自己的视线,扫过薄唇时微顿,最终落在楼准的鼻尖痣上,他眼神飘忽地看了片刻,许久后像是下定了决心。
靠在进门台上的腰有些疼,他干脆起身,把重心全部放在楼准身上,在楼准慌忙着抱住他的时候,刚刚落在喉结上的唇又落在了那颗痣上。
“它。”
他轻轻磨蹭了一下,两人的鼻息纠缠在一起。
今夜的他比之前都要大胆。
楼准只要低眼,就能看见薄朝明显的不清醒的带着情欲的眼。
他靠在了紧闭的门上,薄朝整个人都靠在他怀里,只是沾染上薄朝身上的酒味,他好像就醉了。
“那你为什么要戴眼镜?你明明不近视。”仅存的理智让他问道。
那双勾人的眼睛看向他,像是被水润过一样,晶莹剔透,明明戴眼镜会挡住这双漂亮的眼睛才是。
“因为,”薄朝凑得更近了,声音软下来,“这样我会更敢看你。”
楼准抚在薄朝腰侧的手骤然顿住,顷刻在薄朝再次离开时就想上前,但刚刚贴着他的小猫推开他,嘟嘟囔囔道:“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在我梦里出现,我亲了又没反应。”
“这次还问这么多无厘头的问题。”
他下着结论:“无聊。”
薄朝走路歪七扭八,扶着进门的柜子有一步没半步,在即将进入客厅的时候,他随意甩在身后的手腕被牢牢抓住。
下一秒,他又靠上了温热的胸膛,他的腰被另一只手环住,刚刚抓住他的手松开,下颚被扼住,下巴被迫微抬,嘴唇上传来从未有过的触感。
他的眼睛还没闭上,于是在最初的恍神后醒来对上了就是楼准带着笑意的眼。
楼准只是轻轻一啄,看着薄朝怔楞的模样干脆把人打横跑起来,这动作他在游戏里已经做过无数次,环抱着腰的手,恰到好处的力度,和怀里熟悉的人都让他身心愉悦。
在把薄朝扔到床上后,楼准俯下身,乌黑的眸子明明带着笑意但从上方俯视时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薄朝有些后悔摘下楼准的眼镜了。
他笑着,牢牢钳住薄朝放在床单上的手问:“这样的反应够吗?”
“为什么只亲喉结和鼻尖?”
他歪头俯身,黑色的碎扫过薄朝的脖颈,很痒很陌生的感觉让薄朝不由得颤了颤,但手被抓着,他每动一下都像是无意识地迎合。
楼准咬了回来心情很好,又在薄朝下巴处吻了一下,薄朝仰着头脆弱的部分都展露在楼准眼里,泛着红的脖颈和隐隐带着牙印的喉结。
醉酒的人没什么力气,没撑多久就倒在床上,急促的呼吸就在耳畔,楼准就着他的位置侧身躺下,蹭上那只已经通红的耳朵问:“其他地方呢?”
身下的人睁着那双朦胧的眼睛,泛着水汽让楼准看不真切,温热的物体开始靠近,后颈被酒后烫的皮肤贴上,一寸一寸的热量顺着胸膛传到砰砰跳着的心脏。
薄朝费力地抬起上身将双臂勾在楼准脖子上,仰起头,视线飘移半刻后轻轻落在楼准的薄唇上,他盯了片刻,在手臂力气即将耗尽之前偏过头,又是一个轻轻的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