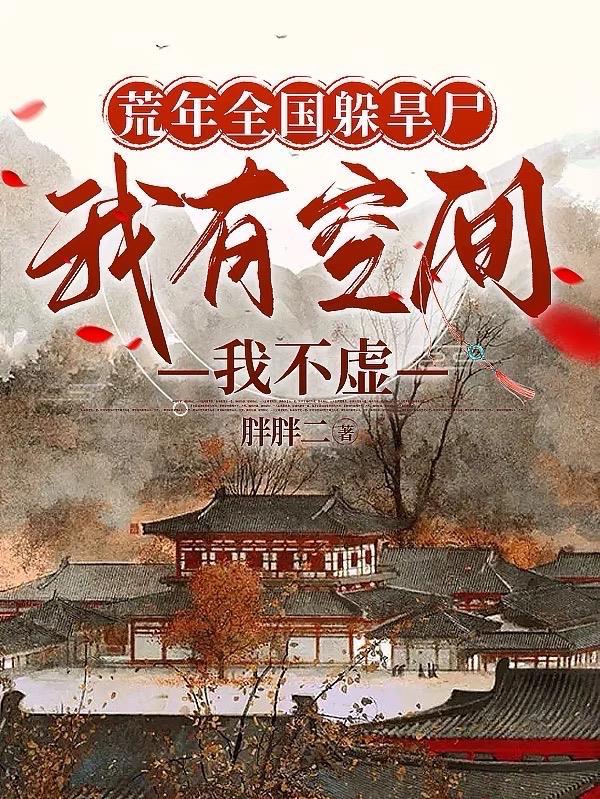凤阅居>我穿越到了终极笔记 > 第4頁(第1页)
第4頁(第1页)
朱氏渾身發顫,抖得像個米糠篩子,沉默著點了點頭。
錢管事辦事態度也算得上親和,就因為他親和,所以何東來給他準備了五個彪悍的夥計,他嘴邊的旱菸還沒有散去,不緊不慢,輕描淡寫地又說道:「那脫衣吧。」
這種親和是一種冷血的親和。
受鞭刑,男子都會被扒去上衣。
錢管事稀鬆晦澀的眼珠子一點都沒有波動,依舊緩緩地吸著旱菸,五個夥計卻露出了猙獰譏誚又猥瑣的神色,待要去伸手,朱氏低垂著頭自行開始解上衣的領子和繩結,她是游娼,從不吝嗇將自己的身子給人看,頭一次她還忸怩過,但那掙不到錢,後來她的羞恥心就成了米糠中夾雜的砂礫,搖搖晃晃搖搖晃晃就被篩子篩了出去。
但面對圍觀的同村鄰里,她不做人了,她的孩子還要做人。
等脫了身上那件補了又補的短襖和中衣,她顫巍巍地低聲哀求道:「各位村民鄉長,請愛護我家趙興。」語罷,款款彎背,不疾不徐地磕了三個頭。
少交一兩租,要受一鞭子。
她少交十兩,就要受十鞭子。
前兩年也有人為了省一兩受過一鞭子,就讓家裡最強壯的人去挨,然而那個人到現在都直不起腰來,成了家裡的拖累,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為了省銀子去受這一鞭子了。
後來聽說錢管事身後的五個夥計都是在官府刑獄司練過的,鞭子在他們手裡不是鞭子,是刀劍,稍稍用力的一鞭子就能將一個壯勞力廢掉,可他們只是交不起租的佃農,並不是什麼十惡不赦殺人奪命的罪犯。
是以朱氏認為,她應是活不過今日了。
這是臨終託孤。
村民們有老者有孩童有婦人眼眶驀然紅了,有人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悄悄抽泣,緩緩轉過身去。
沈蕪沒有轉身。
她看著院中的這一對母子,身體在寒風中逐漸發熱,血液從她的四肢百骸滾滾涌動,像點燃的柴火堆,一股一股滾燙的血液匯進她的心臟,激動著她的心臟,讓它躍動得越來越快,眼眸嘭地點燃兩簇火苗,手指蜷曲進手心緊緊攢成拳,身上的肌肉崩得極緊,咬著牙關,像一張蓄勢待發的弓,等著射出去的那一刻。
千鈞一髮之時,朱氏又緩沉地對她磕了一個頭,對她一個人。
沈蕪僵硬地轉了身。
還不是時候,沈蕪知道,還不是時候。她今日幫了她,那她的孩子怎麼辦?漁利口的佃農們怎麼辦?
他們會被當做暴民鎮壓,會被官府打殺,會死傷大半,會家破人亡。
雖然,他們是毫無反抗能力的暴民。
那日之事歷歷在目,沈蕪的腦中還迴響著劃破天際如響雷一般的鞭聲,噼啪噼啪十下,中間夾雜著女子隱忍地哀鳴和痛呼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
曾經她在史料中讀過佃農被壓迫的內容,內心震撼動容,只是那一點震撼和動容怎麼比得過親眼見過,親身經歷過。
她不要這樣,她不想這樣。
「這天色還早,金銀花還沒曬乾呢。」趙婆婆把碗放下,撿了一朵竹扁里舖開的花朵子在指尖捏開。
沈蕪緩過神來,眼眸中深沉的緩痛漸散,微翹著嘴角說道:「去集市上曬也來得及。」
趙婆婆不懂她話里的意思,只以為她著急賣錢,就依了她。
她們正收拾準備走,趙興又從前頭跑了回來,或許他回想起去年冬天的悲慘往事,或許是怕自己的憤怒惹禍。
沈蕪揮揮手讓他來:「趙興,我和婆婆要去鎮上賣花,你來幫我們吧。」
收租的日子,如果留他一個人在家,一個沒有寡婦娘親的家,他應該會難過吧。
趙興跑了過來,笑得勉強:「傻姑,大黃去不去?」
一老婦一少女一小兒身邊穿來穿去一隻大黃狗,身後是灰煙滾滾的邛崍山,身前是通往鎮子集市的大道。
沈蕪是第一次來魯鎮,魯鎮很大,街道上都是人,他們很像熱鍋上搬米粒的螞蟻群,怕燙了腳,又怕掉了貨物,所以攢動得又快又急。
「好長時間沒有見過這麼多人了吧?」趙婆婆看出她疑惑的神色笑道,「三四十個鄉鎮的人都在魯鎮趕集做買賣,唉,大旱三年富人更富了,窮人更窮了。」
沈蕪沒來由地想起前兩天曬米時撿出的一大半細沙。
「這裡有白米粥嗎?」她指著街對面的一家粥鋪問道。
趙婆婆笑得更加殷切:「這裡的粥鋪不僅有白米粥,還有白米飯,白面饅頭,羊肉酸菜包子。」
沈蕪「哦」了一聲,又問:「他們幾時收鋪?」
趙興聽見白面饅頭的時候就吞咽了滿滿一口口水,又聽見羊肉酸菜包子,更是按捺不住地擦了一下嘴角,眼神灼亮地看向沈蕪。
趙婆婆呵呵笑道:「粥鋪一直賣到戌時。」以為沈蕪想賣了花來這裡吃飯,回答得更仔細些,「他們關鋪之前剩下的粥會賣得更便宜,羊肉酸菜包子也半價賣。」
趙興高興地喊了出來:「真的嗎?婆婆,我已經兩三年沒有吃過肉了,今天能吃到嗎?能吃到嗎?」
連大黃狗都嗚嗚地用頭來回蹭沈蕪的小腿,撒嬌乞憐,圓溜溜的眼睛盯著她,就像在說:「真的嗎?真的嗎?大黃我也想吃。」
沈蕪愛憐地一手揉大黃的腦袋,一手揉趙興的腦袋。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