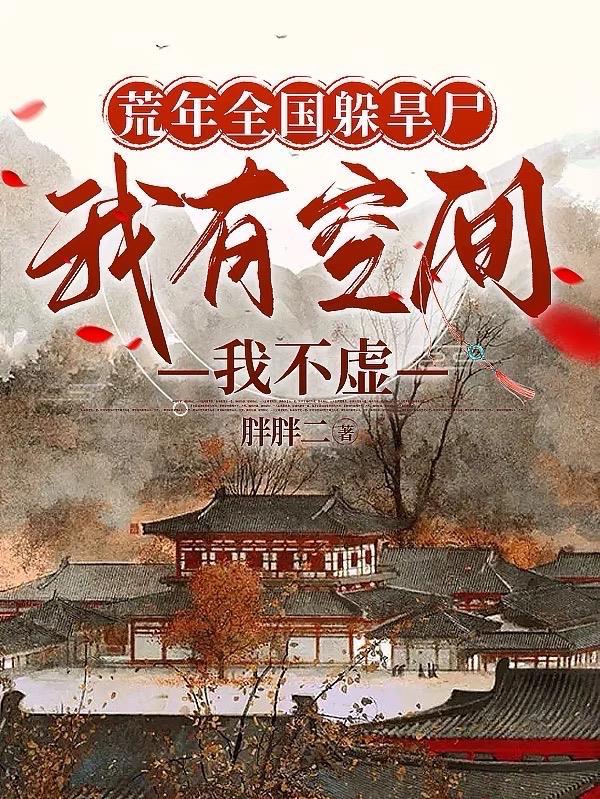凤阅居>无限重生终结后我抛夫弃子了笔趣阁 > 第4页(第1页)
第4页(第1页)
欺软怕硬,趋利避害,大概是大多数人潜藏在骨子里的劣根性了。
经历了许多世的轮回,白驰已掌握了一套如何以最快速度收服沈家人的办法。如果说行之有效,所有的心机筹谋、好言相劝,都不如拳头来的快捷干脆。
她也无需考虑长远,因为她只有最多十一月的时间而已。什么以真心换真心对她来说都是无用。她要的,不过是这段无聊的岁月过的舒坦而已。
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过去,每过去一会,就多一个人进门,或是沈家人或是丫鬟小厮。
轮回次数多了的好处就是,她早已摸清了沈家大宅每个人的脾性好坏,有的人只需吓唬几句便服服帖帖,有的人需要暴打几次才肯老实,还有那墙头草的,这边跟你告饶,回头得了机会就要跑出去报官,那只需一条麻绳捆上,丢在柴房,每日馊饭凉水喂着,不叫他死了,等过些时日,自然也就驯服了。
当然了,府内的下人,还是要以利诱之。
八月的桂花香铺满了整座小院,白驰仍是坐在那张太师椅上,她抬着眉眼,看向西沉的夕阳,事不关己似的。明明日光落在她身上应是暖融融的,可她从上到下无不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像是透着寒气的冰雕。
院内老老小小跪了一地,下人们倒站起来不少,有的手持棍棒护卫在白驰身侧。
有些人,天生就是小人,可他们极有眼色,跟谁有好处,他们就跟谁。他们不管什么忠义好坏,只要私利。这样的人是卑鄙无耻的,不可交付后背,不可长久交往,可这样的人又很好用,只将他们当成咬人的狗,手里的棍棒,指哪儿打哪儿,还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譬如早上叫嚣的厉害的杨婆子等人,分明是秦氏的人,现而今却以白驰的心腹手下自居了。
白驰的手段叫她们惊惧,也给了他们无限底气。内宅的沈家妇人、那些个还算忠肝义胆的忠仆都叫他们治服了。
至于外头的老爷们,几下棍棒下去,也都没了脊梁骨,抱住妇人呜呜的哭了。
院子里敞着十几口箱子,满满的金银铜钱,布匹珠宝,都是从沈府的库房里抬出来的。
“主人,主人。”杨婆子轻声唤她,叫了好几声。
白驰像是思绪陷在迷雾里,终于被叫回了魂,她垂下眼,有片刻的迷茫。
而后她站起身,说:“我是沈家明媒正娶娶进家门的媳妇,那么从今后这个家就由我来掌家了。我对你们没旁的要求,就一个,听话懂事,别惹我不高兴。”她慢慢的走过去。无一人敢吭声。
这些人有的被打服了垂着头不敢吭气,有的被五花大绑嘴里塞了破布。谁人驯服,谁人倔强,白驰心里清清楚楚,无需严刑拷打,抓住一个,或吓或绑,指一个合适的去处,因此小小的沈宅落在她手里,只一日功夫就被她收拾的服服帖帖。
她行过人群,裙摆落在妇人们中间,有人瑟瑟发抖,脸色煞白,有人膝行避让,小声哭泣。
她蹲下身,“四姨娘,你在怕我?”
那被唤做四姨娘的女子猛得就要往地上磕头求饶。白驰轻飘飘的一抬手,挡住她的额头。
白驰的手顺势划过她的脖颈,像是轻薄的登徒子,惊出四姨娘一身冷汗。
她的手轻点四姨娘盖在衣领内的淤青,最终落在她袖子内的手臂上。
不知何时,她的袖子被掀开,露出陈年的旧伤,斑驳的痕迹,叫人不忍直视。
“这些年,过的很苦吧?”她的语调依旧轻柔缓慢,像是挚友亲人,直叩人心,四姨娘的眼泪忽地就落了下来。
被捆缚住的几人中,有人不安的动了动,一双血红的眸子死死盯住她。
白驰笑了笑:“既是过的如此不堪,我给你一条活路可好?”她站起身,四姨娘不由自主随她一同起身。
白驰轻车熟路将她带到那名眼眸血红的男子身边。这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长的高壮结实,面皮有些黑,看面相就是个忠义可靠之人。
“我这个人吧,最见不得女人受苦。沈家既由我做主,那我就放了你,叫你和你的情郎远走高飞可好?”
那名男子同四姨娘双双变了脸色。
白驰抽了护院手里的刀,也不见她怎么动作,男子捆在身上的绳索碎了一地。
男子拨掉嘴里的团布,大怒,“你休要胡言!我同……同四姨娘清清白白!”
四姨娘仰面看她,却一时没了声。
白驰长的高挑,长眉英目,她低下头来,冲她笑了笑,“我只问你一句,这牢笼般的沈家,你是想留还是走?机会只有一次。”
四姨娘咬住唇,几乎咬出血来,“我的孩子……”
白驰:“可以带走。”
四姨娘晦暗的眼忽然光彩大盛,她几乎是跪爬着扑到白驰腿前,郑重的磕了一个响头。扭过身就拉住了男人,“庄田,带我走!”
男人只犹豫了片刻,一狠心,也朝白驰做了个揖,随同四姨娘一起从人堆里抱出一个小小的刚满一岁的女娃儿。
女娃不是男人的骨肉,但四姨娘却是他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要不是沈家三爷强取豪夺,他二人早就结做夫妻,儿女成群了。
这么多年,他二人一个内宅妇人,一个外门管家,偶儿碰面,也都装作不识,从未有过不合礼数的举动。
所有人都吃惊的看向他们,面上神色各异,有震惊难以置信,有憎恶怨恨,也有羡慕,还有激动和鼓励。
四姨娘谁也没看,同庄田互相搀扶着,抱着孩儿正要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