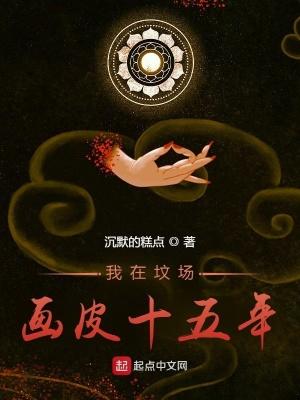凤阅居>义姐是不良哺乳的动物喂养中 > 第78章 第 78 章(第2页)
第78章 第 78 章(第2页)
宴卿卿微微张了张嘴,忽然想问他昨夜在哪儿,可话到嘴边,却又一句都不敢问了。
闻琉与她视线相视,稍稍俯下了身子:“义姐要说什么,不用太大声,朕凑近听就行。”
他眸色浅灰,仿佛一眼能望到底,倒不像心思怪异的放荡小人。宴卿卿心中压抑更甚,她恍惚觉得昨夜不像梦,但那不可能,闻琉是守礼制礼的,换做是谁都不可能是他。
他没理由在相然和钟从凝的面那样待她,那些下流的动作更不可能是他所做。
轮定安这药,或许就是要利用这来毁人心智。
“让他们都下去。”她闭了眼,轻轻道,“我有事要与陛下单独说。”
“待会再说,朕医术不好,怕开错药,让御医再给你看看。”如玉的手指轻轻将她额角的丝扒到一旁,闻琉这个动作十分温柔亲昵。
相然刚抹掉把泪,手放下来便见到闻琉这举动,她的手顿在了原地,心觉这动作不妥当。她在一旁欲言又止。但宴卿卿轻应闻琉一声,似乎又并没有觉得不对。
闻琉转头瞥了两眼御医,御医连忙过来,在宴卿卿白皙的手腕上盖了层薄纱帕,轮流替她诊断起来。
这两位都是老御医,质资品性都信得过,医术高。在上马车之前便有人吩咐过他们,无论诊出什么病症,都不许胡言乱语,否则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他们还以为是皇上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病,倒没有料到是这位宴大小姐。见宴卿卿脸上的苍白,御医怕是什么大病,不由小心翼翼了几分。
低奢的马车中安静无比,时间慢慢流逝,马车边置着暖炉子,明明是恰好的温度,御医鼻尖之上却冒了薄汗。
御医看了宴卿卿,见她闭着眼睛,便又转头看着闻琉。
闻琉正在轻声对宴卿卿说话,像是在跟她说没事,这位帝王的眸中只有她的影子。
御医眼皮倏地一跳,像是现了什么东西。
手下的脉象滑而有力,有轻微的珠滑圆润之感,而尺脉按之又是不绝,这分明是女子怀胎足月的脉象
在宫中活得久的御医,都是人精。宴大小姐许多宫里人都认识,她是宴家孤女,守宴家偌大财产;又得皇帝敬重,称为义姐。
宴卿卿现在尚未成婚,而皇上此时又是这般担忧模样这腹中的胎儿,怕是来得不简单。
御医见过不少宫廷秘事,可无论哪回见,都是吓得腿肚子软,闭紧嘴不敢乱说话。
这胎像并不太稳,隐隐有流产的征兆,该是早就出事了,若等他们现在才过来诊脉,这胎儿可能已经没了。
此时却什么事没有,怕是已经喝了安胎药。
御医敛了心思,不敢出任何的声音,收了薄纱帕退到一侧,手心出了薄汗。
另一位御医上前,摸出这脉象后,他与那位御医是同种心思,均是额上冒冷汗。
闻琉把宴卿卿的手放回绣黄龙纹棉褥中,抬眸问道:“如何”
两位御医不敢胡乱说别的,只道了方才来时侍卫教的话。
“宴小姐是受了什么刺激,以后小心些看护就好。”御医迟疑着说,“最近还是养着些,否则怕是会出意外。”
闻琉又道:“自是会养着可有什么不对劲”
御医低着头,额上的汗珠豆大般,他们只能斟酌着道:“该是与陛下诊出来的相同。”
闻琉静默许久,微微颔了,让相然与御医先退出去。
相然犹豫片刻,见自家小姐睁眼朝她摇了摇头,便只能行福礼出去侯着。
闻琉问:“义姐有什么想对朕说的”
宴卿卿伸出手攥住他的袖口,视线与他相对,葱白的玉指白皙柔嫩,便连指甲盖都圆润光滑,她想和闻琉说那轮定安的事。
宴卿卿再也受不了那东西了。它会挑着暧昧的环境,所有的一切如梦般真实,甚至还会特意营造梦中人与物,让人分不清幻境与真实,宴卿卿怕得要死。
她是宴府的大小姐,便是再怎么样与旁人行夫妻之礼,也该是保守安分的,哪受得了那些出奇的花样
即使是快活,也不该是与闻琉
可到最后,却还是碍于做姐姐的面子,只问了句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闻琉笑了笑,起身先给宴卿卿倒了杯温水,他慢慢坐于床沿边上,轻轻揽住她的细肩,扶她起来,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
宴卿卿的里衣没系紧,他这样一番动作又轻滑下了几分。她有些尴尬,不习惯与闻琉有这样的接触,但身子乏累,没有推开他的力气。
闻琉却抬手将她的里衣遮了遮,倒是没有顾忌,亲近过了头。
“陛下勿要与我这样,”宴卿卿叹了声气,“旁人若是见了,会误会。”
闻琉却是淡淡笑着,将精致的釉杯拿近些喂她。宴卿卿喉咙正是干痒,也不逞强,便轻轻抿了几口。
她和闻琉关系非普通人能比,哪里可能会因为一个梦境就真的疏远他
“现在在马车上,熬不了药,”闻琉把手上的瓷杯置于一旁,遒劲有力的手臂环住宴卿卿,下巴轻轻抵着她的头,“不是大病,不要担心。”
宴卿卿被他这些黏乎的举动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的身子无药可救,心紧紧一缩,问道:“莫不是治不了”
“姐姐还年轻,怎可能得有这种病”闻琉说,“你身子底子还行,不像别家小姐那样孱弱,虽说在云山伤过一次,但养了许久,也算是养回来了。”
“姐姐让朕抱会儿,朕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也就只有以前被欺负时见到你,一直都想谢谢姐姐。”
闻琉的话说得没有缘由,让人摸不着头脑,连他自己都禁不住笑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