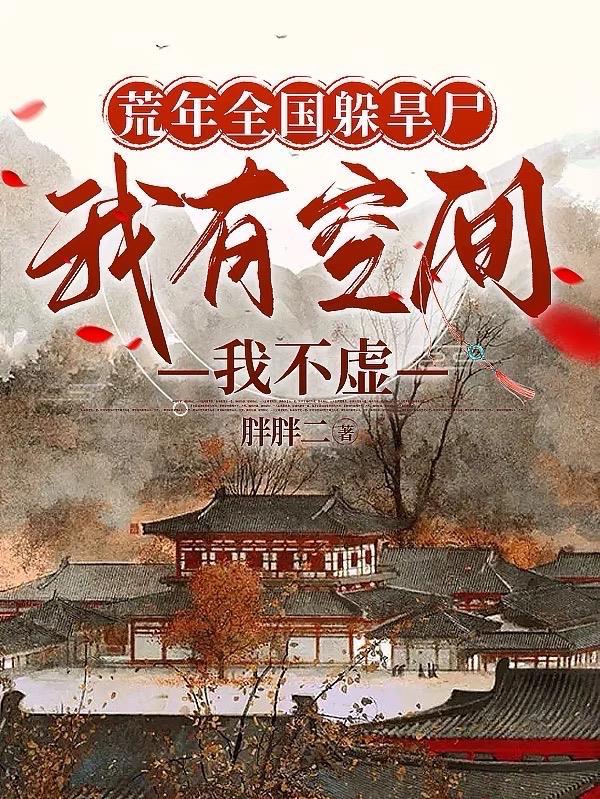凤阅居>清国倾城之摄政王福晋校草 > 第一百三十八节 永离别(第1页)
第一百三十八节 永离别(第1页)
室内很冷,和外面没什么区别。北风从敞开了的窗子里呼啸而来,也挟卷来玉屑琼花一般的雪末,散入珠帘,湿了罗幕,狐裘不暖,锦衾生寒。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从身体到内心,似乎都被这份寒冷彻底地感染了,仅有的一丝温暖,也跟着丧失殆尽。
尽管眼下是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时刻,可今晚不知道怎么的,月光格外地温柔,伴随着被北风拂落的雪花漫洒了一地,冷冷清清的,却好像在无形之中伸出手来,怜惜而又无声地抚摸着我。这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曾经对它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珍惜,可当我真正失去之后,才突然觉,它已经深深地渗入了我的肌肤里、血液里、骨髓里,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摆脱这种依赖了。
似水流年,当我以为我已经牢牢地掌握住幸福的时候,却并不知道,幸福已经悄无声息地从我的指缝中溜走,恍如长沟流月,来去无声。春去秋来十七载,原本以为漫长,可现在才知道它的短暂。我现在才迷途知返,是不是太晚了?
床榻上空空荡荡的,可我明明看到枕边、被角、床帏,都沾染了斑斑血迹,床沿下的地毡上,很明显地染红了一片。这颜色,殷红殷红的,好像还未干涸,尚且残留着生命的温度,仍然未冷。
我的眼前蓦地一花,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天地之间都陷入了苍茫空旷的雪白之中。我努力地睁大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向前奔跑着,因为前方有几簇鲜艳的红梅,在白色背景下格外地殷红,格外地妖冶,仿佛可以淋淋漓漓地滴淌出鲜血来。
可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接近它。它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像落山时候的日头,我就算喝干黄河的水,饮尽长江的水,锲而不舍地一路追到海角,追到天涯,直到耗尽最后一分体力,重重地倒伏在地时,我还是无法用我的手指触碰到它半分。
我站立不稳,无力地软倒在地。可我尚未失去知觉,因为我懵然之间,似乎落入了一人的臂弯,瘫软在他的怀抱。
那人说话了,声音很低沉,很沙哑,带着一点点颤抖,绝望到没有一丝生机,可他说话的内容,却将我从朦胧混沌的世界里拯救出来。
"哥,你快看看,嫂子回来了,回来了。。。我没骗你吧,她真的回来了。。。"
我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急促地喘息着,紧张地问道:"你哥呢,人呢?哪里去了,怎么不在这里?"
多铎起身,将我搀扶起来,"在那里。。。他等你很久了,都快睡着了,你快点过去吧。"
我的两腿仿佛不听使唤,几乎无法自己走路,只能任由他连抱带拽着,一点点地挪到了椅子前。我只看了一眼,就跪倒了,再也无法爬起身来。
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淡淡的月光柔和地洒落在他的身上,给他全身都染上了一层皎洁明净的银色,他身上的白衫仿佛吸收了月的光华,如同在月夜下春江,滟滟潋潋,倒映了毫无纤尘的皎月,伴随着轻盈舞动的飞霜,缓缓地向东流去。
他并没有睡着,仍然睁着眼睛,定定地望向前方的虚无,好像在等待着什么,盼望着什么。他的眼神,一如我当年初遇他时,那般地温柔和清澈。曾经的戾气和冷酷都消失无踪了,一切都归于初始,简单而又纯净。
我很费力气地伸出手来,一点一点地接近他的手指,轻轻地触碰到了,却丝毫也不敢用力,好像他很累很倦,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不敢把他从宝贵的睡眠中惊醒一样。终于,我握住了他的手。
很冷,很凉,比此时地面上的雪花还要寒冷许多。我用双手笼罩过来,覆盖上去,希望能够用我的体温,勉强缓解一下他手上的寒冷。若他还能感觉到一点点温暖,该有多好?
奇怪的是,我还能言语,并且语调还是平和正常的,和平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对多铎说道:"这么冷的天,你怎么能敞着窗子呢?你哥身体不好,受不得风寒,还不赶快去关上?
他在我背后,生涩而艰难地回答道:"是我哥让开的。他说胸口很闷,透不过气来,让我敞开窗子。。。还说这样被冷风吹吹也好,能保持清醒,免得待会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就看不到你回来了。。。"
我一面听着,一面继续地暖着多尔衮的手,看着他手背上那道陈年的伤疤。这既是见证,又是烙印,是我加之给他的,足足跟随了他十七年。也许,今后还会牢牢地跟着他,被他带走,到下一世,或者下下一世。若我可以不喝孟婆的汤,那么只要我还有和他重逢的机会,哪怕他容颜改变,哪怕他见我不识,笑问我从何方来,我也能够一眼就认出他来。
可是无论我如何努力,都没能给他带来任何温暖,倒是我的脸上,有了凉冰冰的湿意,好像清晨时分,走入林子,分花拂柳之时,打落我一身一脸的露珠。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粗糙的手指,一如他以往同样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鬓;我手扶着椅子起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一如他以往同样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嘴唇;我小心翼翼地坐上他的膝头,偎进他的怀里,一如他以往同样小心地将我揽入怀中,怜惜地拍抚着我的后背。
他给我温暖,给我呵护,给我爱。可我现在,却什么也给不了他。甚至连他临走前的最后一次等待,都不给他个等来的机会。或者,我给他的仅仅是绝望和悲伤,以及无尽的遗憾。他是不是在恨我,怨我?我不肯来听他最后的道歉,我不肯给他一句原谅的话语,甚至不肯让他看到一滴眼泪,在为他而流。
我抱着他,在他冰冷的唇上落下温情的亲吻,他总是抱怨我不肯在亲热的时候对他主动,我从来不肯主动地亲他。现在,他所期望的东西来了,可他再也不能听,再也不能看,再也不能感受到了。
过了半晌,我方才问道:"他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走的?"
多铎呆呆地望着我,失魂落魄,眼神如一潭死水般呆滞,好一会儿才勉强回答:"就在你进来之前。。。他说是躺在床上喘不过气来,要坐在这里等你。我就陪他坐着,看他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他最后一次醒来时候天都黑了,说是胸口很疼,要我给他揉揉。起初他还小声呻吟,到后来,就渐渐地没声音了。我还以为他睡着了,可一抬头,却看到他明明是睁着眼睛的,好像还在巴巴地盼望着你回来。再一摸心口,就没有半点动静了。。。刚好这时候,你就进来了。。。"
到后来,他已经说不下去,难以为继了。为了掩饰他的痛苦,他不得不双手掩脸,背过身去。我虽听不到他出任何声音,却依然能看到他的双肩在微微地耸动着,我知道他正陷入在极度的悲怆之中,不能言语。
终究还是没有赶得及啊。
时间有时候很慷慨,这么多年过去,都没有让多少沧桑爬上他完美的脸庞,和当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丝毫不见衰老的痕迹;可时间有时候却是极度地吝啬,它甚至不给他多一刻的时间,让他最后看我一眼,让他因为我的到来而最后地微笑一次。
本来我应该是被安慰的那个人,可奇怪的是,我居然反过来安慰在悲痛中不能自已的多铎来了:"别伤心,别难过,人总是要走的,没有人能够永远存在,将来你和我,也是要走的,想开点。。。其实,这未尝不是好事。他这些日子来,弄得遍体鳞伤的,虽然还活着,却比死了还要难受。。。再说,他已经很累,很倦了,再让他这样辛辛苦苦地支撑下去,才是更大的残忍。不如,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了吧。以后,他不用再为什么人,什么事操劳辛苦,不用在长久的后悔和愧疚中挣扎煎熬。他现在算是,彻底地解脱了,轻松了。"
"可是。。。"多铎刚刚回了个开头,就说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力压低了的哽咽声。
他似乎比我还要伤心。也是啊,我的心早在半年以前就彻底地死掉了,以后虽然仍然会痛,仍然会酸,却只不过是些幻象和自我安慰罢了。凤凰可以浴火,可以涅槃重生,可我不是凤凰,我不会。
我明白他后半句想要说什么。他是在替他的哥哥抱憾,因为他哥哥终究还是没能等到我来,没能亲口说出饱含歉意的话,没等得到我的谅解。只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又哪里能没有点缺憾,爱情又哪里能彻底地圆满呢?
我曾经刻骨铭心地爱着他,又曾经刻骨铭心地恨着他。可是无论如何,时光如水,能冲刷掉一切;又譬如大浪,淘去泥沙,留下黄金。正如我可以忘却他对我的恶,记住他对我的好。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他,和他脸贴着脸,好像他仍能听到我的话语,感受到我的温情。
"皇上,有些话就算你不说,我也明白。我的确曾经误会过你,可我现在完全懂了。我总是抱怨你对我的伤害,可是我又何尝没有伤害过你?你我的爱意,太激烈,太炙热,也太决绝了,容不得一点误会,一点妥协,才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你有愧于我,我也有愧于你,咱们这就算是,扯平了吧。。。至于东青的事情,我后来也知道,那不是你的本意,你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他死,只不过你能战胜了一切敌人,却战胜不了附着在你身上,心里的魔鬼。也许,这就是命运弄人。
分离的这些日子里,你应该一直沉浸在痛苦和负疚中,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吧。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惩罚你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也不快乐,一点也没有报复解恨的快感。莫非,我心里还有你,不论你是好是坏,你始终是我最爱的那个男人,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我知道他已经听不到了,我就算竭尽所能,都无法唤回他的呼吸,他的心跳,他的魂魄了。他再也不能微笑着注视我,再也不能温柔地替我擦去泪水,再也不能对我说:"熙贞,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抱着他渐渐冰冷的躯体,回忆着他曾经给我的温暖和保护,说着道歉和原谅的话给自己听。他是如此强悍的男人,强悍到他死后我还会蜷缩他的怀里,趴伏在他的肩头哭泣。若是他下一世,下下一世,还能继续保护我,给我温暖,该有多好?
时间悄悄地流逝着,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的泪快要干涸了,却依然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我看着他曾经明澈如湖水般的眼眸渐渐变得迷朦,摸着他的胸口,连最后仅剩下的一点点温暖也彻底消失了。我徒劳地紧合手掌,掬护着他的生命之水,阻止它那么迅地流失,可无论我的手合得多么紧,那水还是从我的指缝涟涟不绝地漏下去,漏下去。一切都有如镜花水月,无论是杨柳依依,还是雨雪霏霏,都随着他的逝去,而彻底地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嫂子,你松手吧,再耽搁下去怕要僵硬了。"多铎在我身边轻声地提醒道。
"嗯?"我愣了一下,见他拉我的手臂,明白了。我并没有阻止他,而是点了点头,缓缓地从多尔衮的身上下来了。
多铎来到他跟前,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伸手过去,将他抱起,重新放回在床上。我跟随着来到床前,默不作声地继续凝望着。
"嫂子,你看要不要。。。"
我明白他要问什么,迟疑片刻,终于还是答应了,"好。"
多铎最后看了他哥哥一眼,然后抬手拂过。我再看时,他已经阖了眼睑,仿佛安详地睡着了,没有什么人能够再打扰他的休息,打扰他的安宁。
我正呆呆地望着,多铎已经把我襟前的丝帕抽去,展开来盖在他的脸上。最后,拉起被子,将他完全地覆盖住了。
这一瞬过后,我心中仅存的支柱也彻底地崩塌,轰然倒地了。胸腔里面空空荡荡的,仿佛我身体的一部分都随之消失,连魂魄也跟着蒸掉了。
多铎出去了,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几乎可以撕裂心肺的悲泣,或者说,那根本就是惨绝痛绝的嘶喊。众人也紧跟着恸哭起来,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
我瘫软在地上,怔怔地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看到帐帘一掀,一人跌跌撞撞地进来了,那人两眼通红,先是呆立了片刻,然后径直来到床前,用颤抖的手去掀被角。
沉寂之后,他终于放了手,缓缓地跪在地上,滴滴晶莹的泪水,掉落在膝前的地毡上,让上面已经干涸的血迹一点点地溶化开来,重新鲜艳。
"阿玛。。。"(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6。qidian。,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