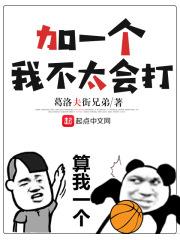凤阅居>朕靠宠妻续命 故栖寻 > 第51章(第2页)
第51章(第2页)
谢折衣应是早料到他会来,大晚上的衣妆济楚,煎茶焚香静候君至。
殿内烛火煌煌,像极了提审罪犯的大堂。
红衣美人灯下览书,也像极了没有感情的冷酷判官。
雍盛一点一点捱进去,摸摸这个,瞧瞧那个,朝怀禄狂使眼色。
怀禄只得硬着头皮再通禀一声:“娘娘,圣上来了。”
谢折衣纹丝不动,连个眼神也欠奉。
阖殿里的宫使也都眼观鼻鼻观心埋头专心当聋子。
雍盛摸摸鼻子干笑两声,自怀禄手里提过一样黄绸缎覆盖着的物事,放到谢折衣面前的案上,兀自坐下,倾身讨好道:“皇后看什么看得这般入迷?”
谢折衣不答。
雍盛四周张望,仍是笑模笑样:“朕瞧着这凤仪宫里的支应人换了不少,也不见绛萼绿绮在跟前伺候。”
谢折衣仍是不吭声,甚至握着书卷调了个方向。
雍盛自讨没趣,边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南极冰川哪家强”之类的怪话,边揭开面前的黄缎。
听得一阵窸窣喀喇的响动,谢折衣目光微动。
余光里,只见皇帝旁若无人地自笼子里捧出一只肥唧唧的凤头鹦鹉,搓了半天鸟脑袋,因无人理他,就自言自语卖起惨来:“唉,宝啊,你爹久病缠身,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恐怕没几年就会一命呜呼,为了不让你在这世上孤苦伶仃被人薅去炖汤,爹煞费苦心,给你娶回一个美若天仙的娘亲。”
什么爹,什么娘,不忍卒听!
谢折衣眉头直皱,轻咳一声,示意他适可而止。
那人却毫不理会,非要强行给他安上一个鸟儿子。
“但你这晚娘吧,虽是个大美人,却是个爱生气的大美人。爹也不知她每天都在气些什么,但惹你娘生气,总归都是爹的错。既然爹有错,就该勉为其难赔礼道歉,你说对不对?嗯,你说对,果然是爹通情达理的好大儿。那么现在问题来了,爹该怎样哄你娘开心呢?”
他自问自答,喋喋不休。
谢折衣气得想笑,放下手中书卷,抬眸定定地盯过去,看他究竟想耍什么宝。
雍盛被眼刀狠狠扎了一记,夸张地哎呀一声,使劲儿扯动鸟脑袋上长长的翎羽:“完了臭宝,你娘瞪你爹呢,好凶啊,快,说点什么缓解一下气氛!不然你爹这婚姻危机过不去,你成了没娘的孩子不说,连明天的皇粮也没了!”
那鹦鹉受到断粮的胁迫,为了父母和谐鸟生大计,不得不忍辱负重扯起嗓子叫唤:“啧,臭宝,来抱抱。抱一个嘛,抱一个,叫声小哥哥~”
谢折衣英气的双眉微妙地挑起。
“?”雍盛当即眼疾手快一把握住鸟嘴,涨红了脸“啧,谁让你说这个?”
边数落边偷眼观察皇后神色。
谢折衣眼里已聚拢起清浅的笑意:“它究竟是管你叫爹,还是小哥哥?”
这人用那种又低又哑雌雄莫辨的嗓音叫小哥哥,雍盛只觉得自己的半个魂儿都被勾了去,稳了稳心神,不好意思道:“男人总是又想给别人当爹又想给别人当小哥哥的,要是能同时满足,那就再好不过了。”
“是么?”谢折衣歪起头,似乎当真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最后也只得承认,“圣上说话总是这般……鞭辟入里。”
“那是。”雍盛得意洋洋地赏了鹦鹉一颗松子,探过身小心试探,“皇后……不气了?”
谢折衣仔细打量那鸟。
那鸟瞪着黑漆漆圆溜溜的眼睛仿佛也在打量他,一人一鸟似乎都觉得对方有些眼熟。
谢折衣屈指逗鸟,将它弯而锐利的喙拨来拨去,漫不经心地答:“我气什么?”
雍盛倒也实诚,主动坦白:“气朕不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命谢府女眷入宫啊。”
谢折衣眯起眼睛嗯了一声,也不与他拐弯抹角:“圣上想通过臣妾笼络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