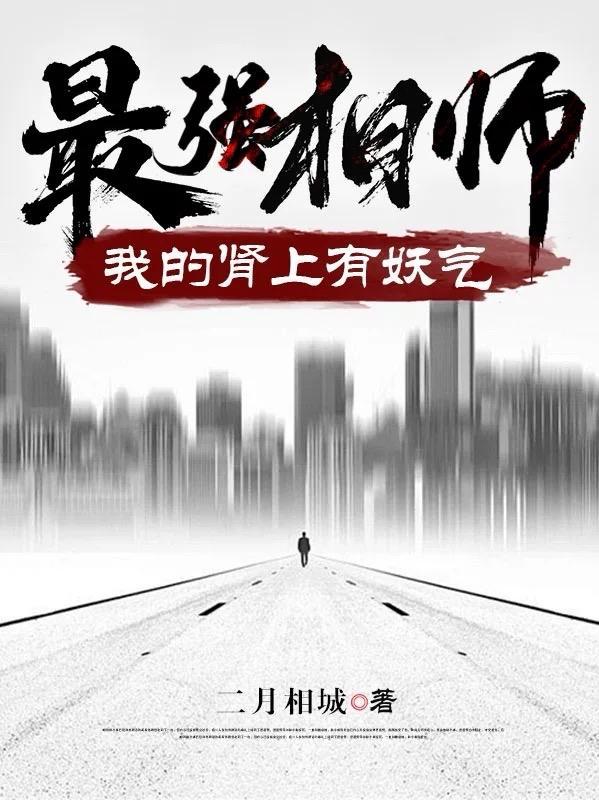凤阅居>朕靠宠妻续命 故栖寻 > 第82章(第3页)
第82章(第3页)
“传令童凇高尚儒谢戎阳,两司即刻起坚守宫门,不准放进一人,违令者斩。”已在脑海中提前演练过无数次,雍盛这会儿应对得还算从容,“再派人前往定国公府,就说传太后口谕,邀枢相进宫陪伴慈驾。”
怀禄面色凝重地领了旨,小跑着去了。
如此危急关头,太后仍能镇定自若地吃完最后一口羹,有条不紊地漱口拭手,在修长的手指上套上锋利的黄金护指。
雍盛才现,太后今日不同以往,换上了庄重繁复的朝服,俨妆盛冠,叫人望之生敬。
“向执这是要逼宫。”
反观皇后,今日却白衣束,略施粉黛,穿着打扮称得上素净寡淡。
太后拍了拍她的手,眼睛却只盯着皇帝:“意料之中的事,勿要惊慌。”
“母后确实不必惊慌,无论是儿臣胜,亦或枢相胜,您总归是清净礼佛,安安心心做这当朝太后。”雍盛的语气透出几分讥讽。
“是啊。”太后叹气,“你胜,他胜,于本宫何异?本宫亦不过傀儡而已。”
“傀儡”一词刺痛了雍盛,他眸色转暗:“所以儿臣期望母后能体谅儿臣的难处。”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太后怜爱的目光落在谢折衣身上,透过谢折衣,她好像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本宫无力体谅谁,只体谅我谢家的女儿,心比天高,命如浮萍。折衣,父亲与官人,如今换你来选,你选谁?”
谢折衣垂目低眉,乖巧得反常,先是像模像样落了几滴泪,又将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演了个入木三分,终于咬起唇,颤声道:“世间难得两全法的道理,儿臣懂,但儿臣实在选不出,假若非要选,儿臣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就清净了,不用睁着眼看这出自家人杀自家人的闹剧。”
雍盛看着她,心里很想笑,却笑不出。
因为他知道,谢折衣虽是演的,但这样的事,确实在某些人身上真真切切地生过,也正在生,或即将生。
“傻孩子。”太后轻抚其背,语气柔软得仿佛不是出自她口,眼神空洞得仿佛望进另一个时空,“既入深宫,从此便再没有什么自家人。你是皇后,还是个没有子嗣的皇后,皇帝在一日,你能当一日的皇后,哪天皇位易了主,你也就保不住你的后位,就跟着没了存在的价值,谢家有的是女儿,而你除了皇帝,没有别的选择。谢家已经繁盛太久了……”
这时,进宝领着莲奴进来,莲奴跪请皇帝示下:“圣上,大臣们还在待漏院候着呢。”
“嗯,传旨下去,今日早朝推迟至巳时。”雍盛道,“再命殿前司拨出一队侍卫前往守卫,一为确保列位臣工的安全,二为提防有人在内策应。另外,今日不论出于何种缘故,点卯未到者,着监察御史一一记录在策,择日另行处罚。”
第83章
巳牌正,雍盛如约上朝,望着底下一众愁眉苦脸如丧考妣的臣工,油然而生一种只有亡国之君才能体会到的悲凉感,哑声问:“枢相人还未到么?”
怀禄答曰:“已遣使问了几回了,枢相近日身子一直不大爽利,恐怕今日仍是来不了朝会。”
这一石头下去,登时激起千层浪。
压抑得好似午夜坟场的大殿中立刻沸反盈天,有肚子里憋不住事儿的武将先声夺人:“这早不病晚不病,一有大事儿就生病,世上哪里凑来的这么多巧儿?光问顶什么用?俗话道,先文后武,先礼后兵,圣上,依微臣薄见,这会儿就该直接派人去将他绑来!”
“你说得轻巧,怎么绑?向执一早便调重兵将定国公府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你让圣上这会儿从哪里寻来个神兵天将,能以一敌百杀破重围将人逮出来?”有消息灵通的呛声。
“诶诶诶,两位同侪未免也太早下定论了,向执不也围了林大人的府邸吗?”
还有不明就里的搅混水。
“那能一样吗?林大人眼下人就站在这儿,他围林府是要用人质来威胁圣上治林大人莫须有的罪,或叫林大人为救家眷甘愿束手就擒!他围定国公府为的什么?你瞧着是包围,我瞧着那铁桶似的阵仗,反倒像是严密护卫!”
“依你之言,今日之变,乃向执与枢相事先合谋?圣上啊,当年您初登大统,尚在幼冲,内外藐圣上年幼,屡屡进犯举事,是枢相大人戎马半生,为朝廷宵衣旰食,日夜操劳,始有今日!而今竟有如此宵小公然污蔑,进馋损抑,臣请治其诽谤之罪!”
“诽谤?朝中何人不知,自二相去后,谢衡独掌朝政,偃然以隐圣自居,擅威福者由来已久,及至朝中科臣畏谢衡者甚于畏陛下,市井小儿知枢相者多于知当今矣!其目无朝廷之制祖宗之法,则亲戚部下群效之,那京营提督向执,即其妻弟,向来以谢衡马是瞻唯命是从,今向执举兵造反……”
“慎言!从何推断向执造反?拿出证据来!”
“你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