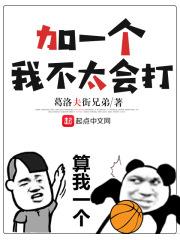凤阅居>地乌金煲汤 > 第23章(第2页)
第23章(第2页)
汪工一头扎进去,并没有看到自己想找的人。
他只知道她叫一号。
只记得她胸口暖白的皮肤、细腻的手指,以及裙子下摆到大腿中上的位置。
前台招待,问什么需求。他只按一小时的价格付了按摩钱,却不肯找个房间躺下来。
“去年三月,你们这里的一号,挂牌子的,现在还在不在?”
这种地方鱼龙混杂,赚快钱的、临时困难救济的,一茬一茬地过,一些新来的生面孔,怯怯地冲他摇头。
只有角落里穿着咖色保洁服的女孩子抬了抬手,“你找…小茹姐吗?”
小茹姐。
汪工一咬这个名字,笑了。
“我找她。”
他擦了擦裤口袋,抹把头发。
“有正经事。”
汪工也就年轻时犯过一次混。
那时候他还在盛泰做工,被同工厂里的组长带出来,说是来体验“韫城特色”。
那也是汪工第一次知道,女人的手指原来是滑的,黑色短袖西装配a字裙,竟然也能穿出不一样的韵味。
他脑子一抽,就喊了句“加钟”。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体验,太快了。
快得他头皮发麻、没几下就弄出来,组长笑话他:“光是岁数上年轻,身子骨不顶用。”
话没说完,一队人乌泱泱地拦到了门口,说是接到了举报电话。相呼应地,隔壁还有赵老板的惊呼、急急忙忙地套裤子。
这桩窘事传的很远。
连季庭柯都知道,汪工差点去蹲了号子。
以至于直到现在,汪工光是看着“小茹”的脸,依旧是一囧。
她似乎比以前胖了,上身换成职业西装、下身齐膝盖的裙子。
还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日子收拾得比他好。
汪工不甚自在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见不得光的地方门路多”,不过是酒过三巡、之后的胡话。
汪工知道,自己不该信的。
他只要随意逛两圈,给季庭柯一个说法就好。
他真的对罗敷的来历,上心到这个地步吗?
不。
汪工清楚:他不过还记得那晚,蹲在角落抱头的自己。
以及吓得跪在床上,衣服被扯了大半、胸前“1号”牌摇摇欲坠的女人。
他想看看,她有没有机会离开这里,以一个蹩脚的借口混进来——
有又怎么样?
没有又怎么样?
汪工道,自己是文盲,想不明白。
大抵,汪工上次来,是还叫“水园”那会儿,店被清查得最狠的一次。
因了这个缘故,小茹隐隐还记得他。
她说:现在的“一池私汤”,早就不附带增值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