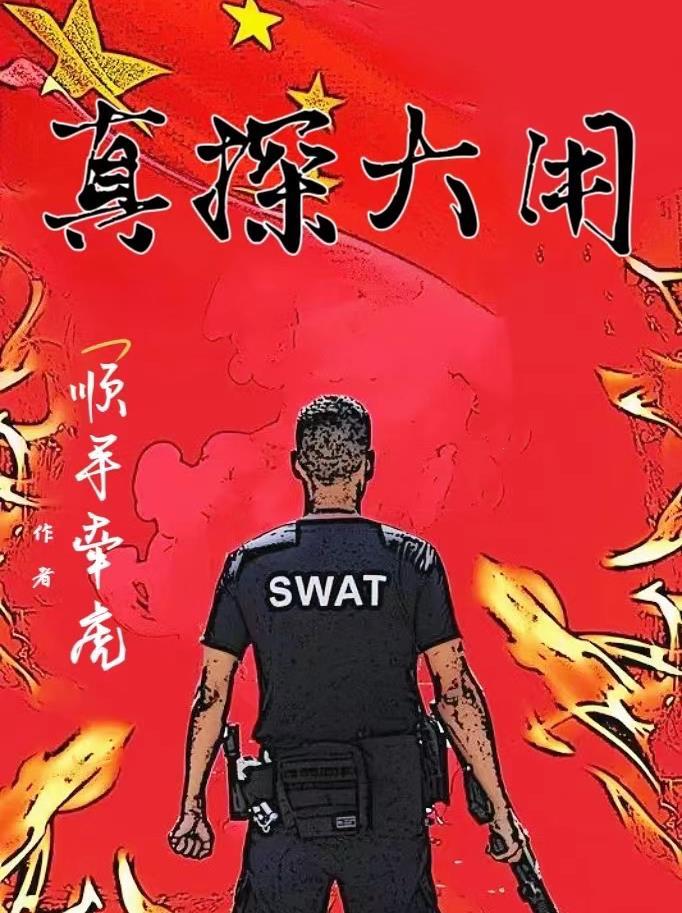凤阅居>庶长子生存守则by从前有只喵喵 > 第36节(第2页)
第36节(第2页)
“我原生家里兄弟姊妹众多,父母便把我们都当玩意儿发卖。妧姨救了我,待我如血亲……可她,却不是个完人……”
明徽胸口莫名一紧,困惑的问道,“什么意思?”
“当年蓝氏夫人怀着双生胎,是妧姨派小丫鬟去惊的。怀王妃也是……被妧姨三两下挑拨,便跟怀王决裂……世子跟你一般年龄,怕是吃的苦头还要多……”
燕斐青是被徐妧儿救下后一手养大的,很多事甚至他也参与其中。当年温柔婉转,美若海棠般的夫人总是嘴角含笑,露出一对米粒大的梨涡。心思却难以琢磨,隐约间带着不顾一切的决绝狠辣。
明徽瞪大了眼睛,一时间被太多的信息砸中,缓了半天才问向燕斐青,“什么胎,什么世子……你把话说清楚!”
可他在想细问,燕斐青已经醉的一塌糊涂,像眯着眼睛软泥般瘫倒在了桌延处,嘴里模模糊糊反复呢喃着些他完全听不懂的话。
因果轮回,报应不爽。
“……”
刚才在席面上,明徽喝的也不少。现下酒意上头,视线朦胧间只感觉中胸口处无边无际的空洞和茫然,心脏在狂跳着宣泄不安,大脑黑漆漆的似沉沦于幻境。
他望着天边一望无际黑暗里永远明亮的那轮月,想了想又摇了摇头。这世上越多烦心事,越要想的开。不明白就不要去想,看不开就不要去看。
你不明白的事太多,别去深究,别去计较。该来的总会来,命中注定的绝逃脱不开。
明徽第二天醒来时,燕斐青已告别徐氏和虞六叔,回衙门处去当值。他洗漱后穿戴整齐,给两人磕头行礼后,还随着小朋友们收到了一份红包,乐颠颠的打开后发现里面还有一签——金榜题名。
“姨妈,你对我这期待也太高了,你说马上就要开考了,万一不中,你岂不是要空高兴一场。”
明徽讨好卖乖的去给徐氏捏肩捶腿,直逗得徐氏拿起帕子捂嘴轻笑,直说道,“你个猴儿,我丢人怕什么,只怕你这次不中,严大人这个师傅却要收拾你”
说到此处,明徽是真的有些心虚害怕。考不中秀才事小,让严光龄丢人事却大了。毕竟此时此刻还图人家美色,万一名落孙山后连个手都摸不上了,岂不是要吃大亏!
“姨母,你说得对!这几日我也不歇着了,谁也别拦着我,我要溺死在知识的海洋里!”
说罢,明徽宛如打了鸡血般雄赳赳,气昂昂的往书房方向跑去。徐氏听的云里雾里,望着明徽远去的背影,只想着这孩子这点到十足十像了姐姐——想办的事,就算费尽心思和气力也要做成。
可命这种事,却是不到最后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谁又知道自己是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呢。
作者有话说:
这其实是一个讲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故事!!
第63章县试
话说县试,用俗语说便是秀才试。
主要在各县举行,通常由知县主持并担任主考官,由儒学署的教谕、训导监考,考试时间是每年的二月份。考试前一个月,各县会张贴公告,公布具体考试时间,这时考生便要尽快到县衙的礼房报名。
到了考试那天,考生需要带着提前准备的文房四宝和食物等考试用品,提前到达考场北面的“龙门”,经过“搜子”搜身后进入考场,在点名后领取考卷,并表明自己是由哪个廪生作保的,获得廪生确认后,便可进入座位答卷。
当然这些不需要严光龄跟自己说,明徽早早便打听清楚。徐氏更是头疼这些问题,年关刚过,院内鞭炮炸出的红色碎屑还未扫尽,她已带着二三小厮丫鬟,跑遍了书斋墨房替侄儿准备停当。
明徽对于这场考试,其实心里并不算太慌。因为县试规定,每场考试要隔数日举行一次,前一场考试通过者才有资格参加下场,且每场考试录取人数依次减少。
而第一场不过考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写的时候要注意格式和字数,不能超过七百字。
拜托,他可是在前世经历过数十年文化教育,虽吊儿郎当,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不至于连最基础的考不过!
等到二月里正式开考的那天,明徽正缱绻在温暖被窝里酣睡的迷糊,徐氏已经起了个大早。
显然对比那位不大靠谱的准考生,她显的更为紧张庄重。一家老小,外加十来个小厮婢女早早被叫醒等在明徽的卧房门口,见到人出来,便说句类似“金榜题名”的吉祥话。愣生生把明徽看的后脊发凉,瞬间清醒。
也是很久之后明徽才明白,所谓的科举出仕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容易简单。
单他只要过了县试,当上秀才,便可见官免跪,免除家族赋税和徭役。就算触犯刑法,也可被宽容一二。正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万千学子无论为了富贵,或是出人头地的机会,或是不同目的,踏上这条路便很难回头的。
这种权利和好处,算是吸引,也算是种让人成瘾的诱惑,接触着皆很难戒断。所以世间才多了无数考到白头都不肯放弃的老翁,也有为了孩子能读书倾尽家产的大户,更多了的是普通百姓家为了家族中一人出头,所付出卖儿卖女的代价。
所以人上人,这是种不公,却也是这个时代能拿出的,最公平的。
明徽在去往贡院的马车里楞楞的发呆良久,徐氏掀开棉帘让他下去时,天还蒙蒙亮着。他刚抬头,便看到一家客栈门口,严光龄笔直的站在那儿。
他今日穿着最普通不过的石青色绣松竹纹常服,旁边的却是个衣着五品官服的老爷。也就是这人剑眉星目,看着便威严而让人不敢侧目,即使什么也不做,在人群里也是亮点。明徽无端心里发痒,跟徐氏说了声后,径直走了过去。
二月里春寒料峭,严光龄常服外还披着一件狐裘毛领的大氅,寒风于天边处吹过,他难免鼻尖被冻的微红。明徽隔着一条街道,故意装出副小狐狸般狡黠而乖巧的模样,含着无尽的笑意,嘴角咧出一对梨涡,顾盼神辉的望着,很是撩人。
严光龄与明徽对视片刻,也跟着嘴角一动,像是笑了笑,也像是说了些什么。招手便把一旁的霍晖叫了过来,叮嘱一二后,便随着穿官服的老爷去了二楼一间被隔断的雅间。
明徽见严光龄不肯搭理自己的挑逗,丝毫没有心理负担。乐天自在的抱上行李包裹,打算跑去跟霍晖扯闲天。
但明显平日里本就不苟言笑,绷着一张肃穆脸的霍晖此时此刻更为紧张,目光发直,贵气的眉眼更生出一股要撕裂众人的煞气。明徽不知旁人怎么看待霍晖,自己心里一阵哆嗦。
怎么这人不像是来考试的,到像是来寻仇的?!
“这场县试,我必得魁首……”霍晖喃喃自语着,茫然中见明徽已经站在身旁,才想起自己又犯了浑病,却也不知说些什么,只僵硬着一张脸,半晌后说道,“抱歉,让师兄见笑了。”
霍晖紧张是有来由的。
因为他自年幼懂事起便心生爱慕的杨姐姐曾经说过——谁若跟他祖父那般三元及第,她便嫁给谁。
从小经历亲爹不管不顾,冷漠刻薄。娘亲暴力倾向,动辄打骂的悲惨童年,霍晖便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且乖戾异常,无故犯浑难过时,只有杨姐姐肯过来安慰自己一二。
“凤屏姐姐想嫁给怎样的如意郎君。”
十岁的霍晖依旧活在无父母亲近的日子中,杨姐姐得空进府里来看望自己。两人于凉亭处吹着带走荷香的微风,十四岁的杨凤屏想了想,一边替霍晖包扎伤口,一边温婉怜惜的笑道,“大抵就想我祖父那般三元及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