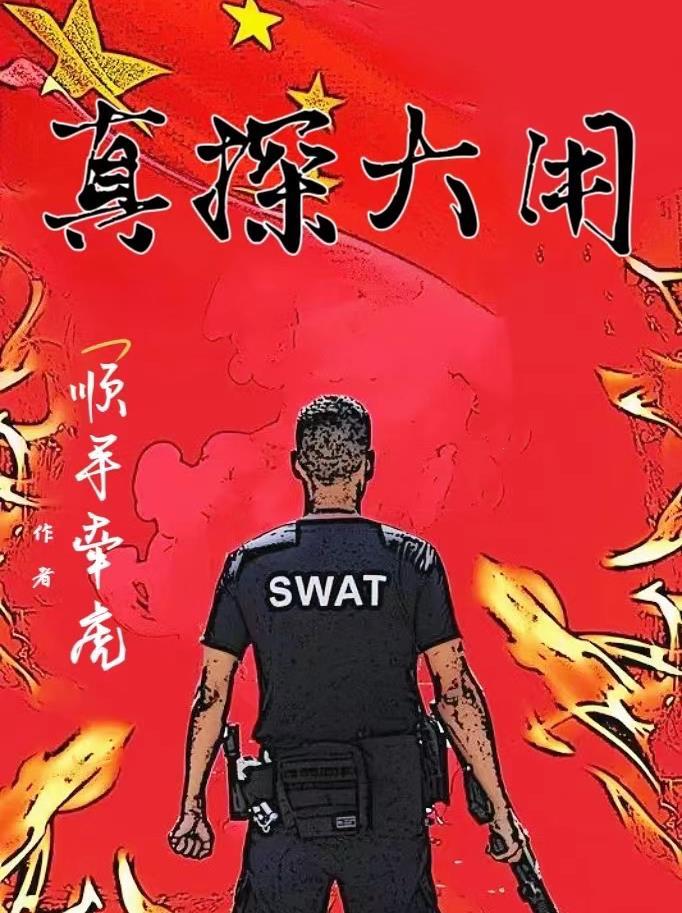凤阅居>还璧归赵的故事 > 第9节(第1页)
第9节(第1页)
要知道,她可是一心想做西装裁缝的人。
可再怎么迎合,终究也仅限于表面。
宋绮年改变不了自已的出身,她永远都只是个小商户之女。同覃凤娇这种金凤凰比起来,她始终是一只小野鸡。
冷怀玉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一定要卖个乖的小人。
见宋绮年有些失落,她越发得意,故意对宋绮年道:“宋小姐,这两日也辛苦你了。眼下也没你什么事,不如早日回家休息吧。和我们不同,你明天一早还得去上班的。”
生怕她留下来分功领赏。
“对,对。”罗太太也道,“尤其是昨天,多亏你替我管家,这家里才没有乱。你先回去休息。等俊生回来了,再好好谢你。”
危机还没有正式过去呢,就开始藏弓烹狗了。
张大小姐觉得不对劲,可又不清楚其中恩怨,犹豫了一下,没有开口。
宋绮年觉得可笑。不是对方,而是自已。
是不是一个社会阶层都还不打紧,但她和这些人的思想情操也显然不在一个境界。
可见财富的多寡,学识的高低,同品德并无直接关系。
宋绮年拿出自已最好的教养,微笑着起身。
“那我就先……”
外头传来声响,人们回来了。
冷怀玉一脸悻悻地瞪了宋绮年一眼。
男人们和覃凤娇走进了书房,各个垂头丧气,这情景简直是中午那个场景的复刻。
覃凤娇呜地一声哭,扑到罗太太怀里:“伯母,是我没用!”
“怎么啦?”罗太太白了脸,“傅老板怎么说?”
“压根儿连人都没见到!”张老爷气急败坏。
“怎么又没见到?这次不是带了画了吗?”
“别提了。”大女婿道,“只派了一个管事出来招待我们,我们说是送画来的。那管家就拿出了另外半张画比对——没对上!”
“啊?画是假的?”罗太太脱口而出。
覃凤娇的脸皮之前在傅老板那里就已经受了损,眼下又被剐了一层。恼羞交加之下,哭得格外伤心。
“我也不知道。堂叔明明说画是真的呀!”
冷怀玉急忙给她挽尊:“咱们又不懂这些。只要能救人,当然是手里有什么,就拿什么出来了。”
罗太太失望之余,还得反过来安慰覃凤娇:“你有这份心就够了。不成也不是你的错。”
宋绮年问赵明诚:“既然都上了门,好歹也要见上一面呀。”
赵明诚没好气:“这傅老板,大概是为了躲我们,临时跑去城外的庄子上打猎去了。”
“那应该去他的庄子上,见到了本人再献画的。”
“他的庄子在淀山湖边上,开车过去得一整夜呢。唉,反正画是假的,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张家眼看就要张灯结彩地庆贺,转眼又被打落地狱。看样子,他们今晚也不会过得多安宁了。
宋绮年无声离去。
她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一间租车行。
不早了,车行正要打烊。伙计见一个秀丽女郎只身前来,神情又楚楚可怜,才暂缓关门。
宋绮年掏出了钱和身份文件:“我要租一辆小汽车,租期一天。喏,我看那辆就不错。”
她指着车库里一辆半新的道奇轿车。
“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劳烦加满油。”
就见这个女郎拉开车门,利落地一脚迈上了车,熟练地发动了车,一脚油门便把车开了出去。
看着那么温婉秀雅,像是个连门都不大出的深宅女子,想不到竟是老手。
深夜马路上车很少,道奇车的尾灯渐渐远去,很快就消失在路尽头。
淀山湖在上海东边好几十公里处,实属荒郊野外。
但那里湖景秀丽,水草丰美。不少有钱人在湖边圈地修庄子,闲来打打野鸭,泛舟垂钓,享受一番野趣。
只是眼下正值隆冬,再温柔的江南水乡也成了阴寒湿冷的沼泽。这个傅老板跑那儿去住着,既折腾访客,也折腾自已,不知图什么?
出了上海市区,越往乡间走,路越烂得好似被轰炸过。
尘土被雨水浸泡成了泥浆,再被车轮碾压,溅满车身和玻璃窗。
宋绮年稳稳地握着方向盘,敏捷地驱车避开路上的水坑。
苍茫的夜,一片浑沌,仿佛盘古还未曾劈开天地。
小小的车灯行驶在黑暗之中,车灯仿佛在大山里挖出一条隧道。
饿了,就吃柳姨准备的糕饼。困了,便停下来睡了两个小时,然后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