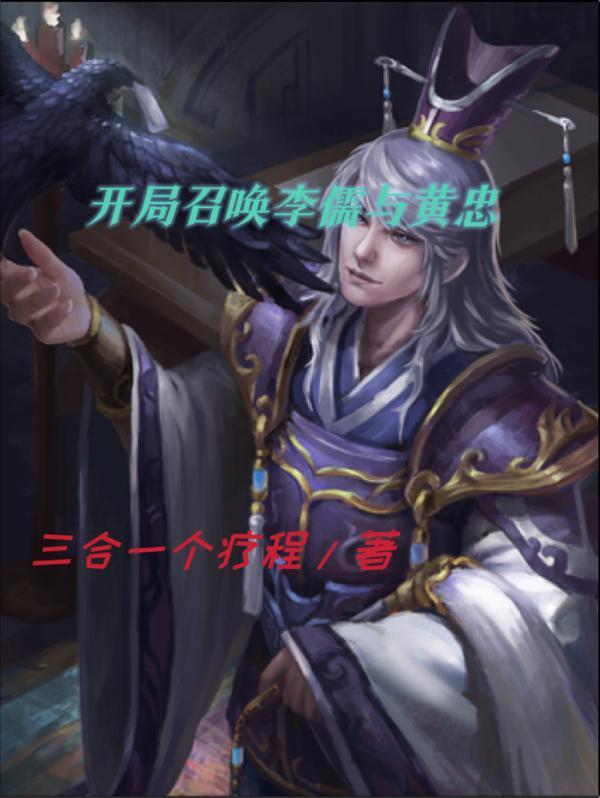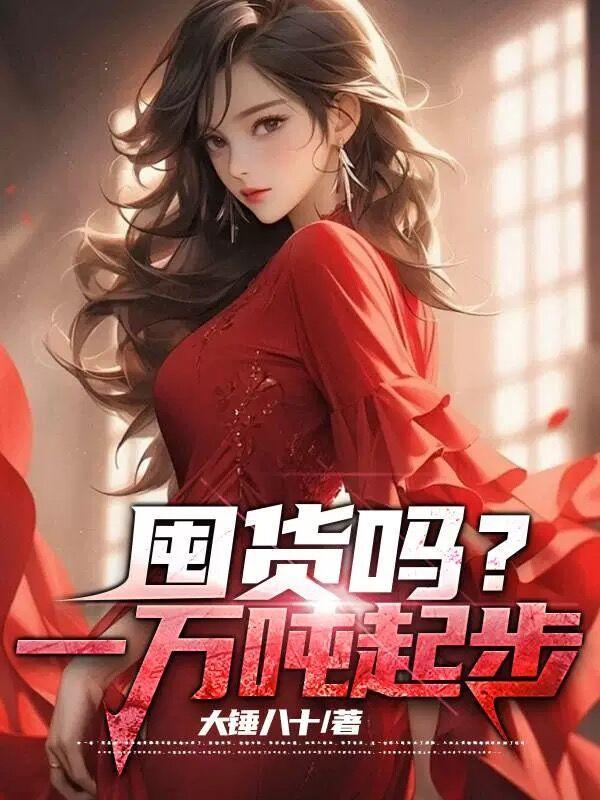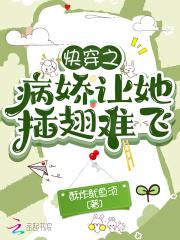凤阅居>综影视王妃 > 第290章 弑君(第1页)
第290章 弑君(第1页)
先被曹党推出来做出头鸟的,自然是齐衡。
齐衡本人瞧不出背后的纷争,甚至无比乐意的接过了这项光荣的使命。
他谏言所选的角度很讲究,没有直言皇后的问题,反而是说皇帝不可过分沉迷于儿女情长之事,应当以国家社稷为主。
后宅丰富则后继有望,如此则江山社稷安稳。
他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赵策英能离他的心上人远一些。
让两人离心,他就开心。
……
又是一月的朝堂扯头花,盛府的爵位被毫无争议的落实了,可关于新帝生父的恩封一事还是未有定论。
朝臣为了妥协,也有提出虽然太上皇于礼仪上有所不妥,可若只是封个王的话……
只是此话刚出,曹党之中也开始生了内乱。
当初认为太皇太后占据年长孝道正统,所以坚决拥护其的朝臣开始了狐疑。
如今的局面并非他们所期待的和平正统与机遇,反而像是一群战场上的先锋队、一个个前仆后继的为看不到正义的战斗去赴死一般。
他们沉默,却自有人高歌。
热热闹闹的,好像满汴京城的人都对新帝有极大的不满。
后宫之中,听闻着今日朝中情况与布局汇报的曹太皇太后正拿着金质的大剪刀一下一下的修剪盆景。
咔嚓,咔嚓。
盆景上的枝丫一簇一簇的落到了台面上。
有细碎的绿,也有成断的褐。
而盆景,却只剩下了主干,还未到霜降却似乎已经迎来了它的寒冬。
把持着剪刀的曹太皇太后心满意足的点了点头,放下剪刀,
“这样看着舒心多了。”
“干干净净的。”
与此同时,恰巧一名年长的内监走进来,低头轻声禀报道,
“太娘娘,都准备妥当了。”
曹太皇太后的笑容愈的收敛不住,她张了张嘴、控制了一下五官与表情,大悦道,
“好。”
从今往后,这皇城内便是她一人说的算了。
……
此时的赵策英刚下朝,正在议事的书房之中与一干重臣再议所谓‘礼仪’一事。
六部尚书除去工部的都来了,御史台的人无论品阶、只要是谏言得到过采纳的也来了数位。
盛紘、以及其三子,连带着诸位同僚,与曹党中的能人干将自然也就位。
两位曹国公,执掌近半数兵权的英国公,在文臣之中颇有威望的辅国公,主打当个挂件但不能没有我的齐国公,没什么存在感、平时非初一十五也鲜少上朝的梁国公也都在。
侯爵、伯爵也有几位,如和葛老尚书家三子说亲了的靖海侯、其嫡女嫁给了盛长枫的中山侯、在与顾家议亲的承平伯,和为人死板、纯粹是自来水的反对新帝恩封其父亲为太上皇的长兴伯。
与其说是私人议事,倒不如说是顶层官员在散朝以后,又拉着皇帝强行继续上朝。
议事殿中,比之朝堂之中少了一些讲究,大家也都借着这个规矩‘畅所欲言’了起来。
长兴伯成了曹党的尖刀,在怒斥着新帝此举与礼法不合的同时,给出了他认为的正确解决方式。
国公是先帝给的恩封,比之寻常国公早已是高一等,提为王也未尝不可,但太上皇……成何体统!
赵策英也没有全盘否决,只是他在委婉的暗示,若想让此事翻篇只需要曹太皇太后归还玉玺、不再垂帘听政。
除去两位曹姓国公拒不退让以外,其余支持太皇太后的官僚、勋爵却开始了思考并权衡起了利弊。
天平似是开始一边倒的时候,敲门声响起。
来者,是已经有孕两月多的皇后。
她习惯性的带着帷幔,饶是对着诸多男眷倒也没有任何的不妥。
而且,皇后早已如此打扮多日。
帷幔自带的半神包裹与边界感,会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留了足够的空间、以让贴身侍女与皇后本人保护好她的肚子。
赵策英对此法颇感赞同,明明只是打扮上的巧思,但却能有如此之多的实际应用,让他很是佩服。
“皇上,诸位大人,打扰了。”
而后墨兰表明了来意,
“太中大夫夫人方才来送了亲手煲的乌鸡汤。